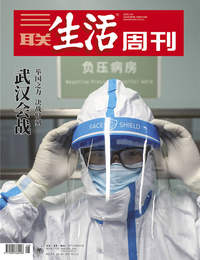韩国电影,从“忠武路”到好莱坞
作者:宋诗婷
2020-02-21·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857个字,产生9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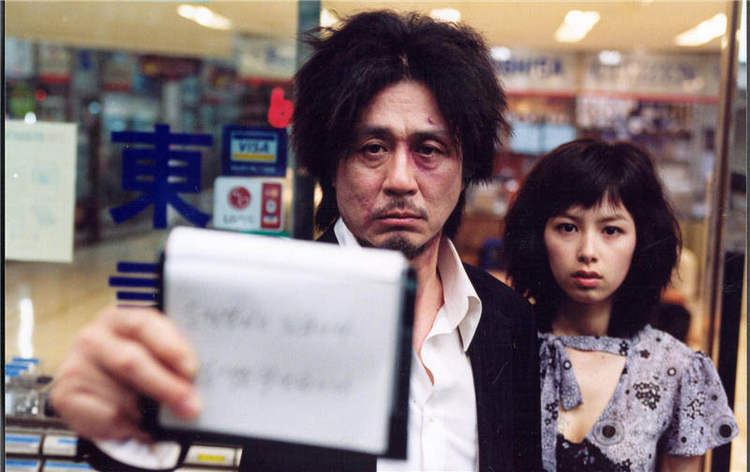
韩国电影《老男孩》剧照
“忠武路”
站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寄生虫》的编剧韩金元说:“美国有好莱坞,韩国有忠武路。我希望能与忠武路的所有电影人和讲故事的人们分享这份荣耀。”
韩金元口中的“忠武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中部,以16世纪著名抗倭名将李舜臣的谥号命名。街道位于南山脚下,北起钟路区的栗谷路,南到中区的退溪路,邻近著名的明洞。那里有上了年纪的剧场,开了几十年的小吃店和咖啡馆,还有装饰得很可爱的宠物店。
就像韩金元引以为傲的,这条街上最著名的还要数那些大大小小的电影制作公司,说它们承载了大半个韩国电影史也一点不为过。
“忠武路”和电影联系在一起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那段时间,韩国政府开始扶持本国电影发展,实施电影税务的优惠、减免政策,政治环境和政策的宽松让常年被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战争和电影审查制度压迫的韩国本土电影有了发展空间。
但这段活跃期相当短暂,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韩国电影政策再次缩紧,重新被意识形态和审查制度把控。“忠武路”真正意义上成为韩国的好莱坞要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那是韩国“新民族电影”全面复兴的开始,也是今天韩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起点。
站在个人审美的立场,除了像李沧东一样的个别导演,我对韩国电影从没有过真正的爱和共情感,总觉得无论爱恨、社会意义诉求,哪怕是幽默,韩国电影都太强烈、太过情绪化了,从未有过举重若轻的美感。
几年前,我从那本《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从哲学和历史视角分析韩国电影的书将韩国的文化美学凝结为“恨”。“要理解韩国的文化现象必须理解‘恨’这个概念。‘恨’是韩国人民所独有的,它与民众对人生、死亡和宇宙的世界观本质上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写过《太极虎韩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驻韩国记者丹尼尔·图多尔(Daniel Tudor)曾总结:“在了解韩国过去所受到的侵略、分裂和战争,以及长期被强势国家压迫的历史之后,就不难理解韩国的‘恨’,里面有认命的意味。”
相信,韩国导演不会反对这种美学上的总结,毕竟,因《追击者》《黄海》而出名的导演罗宏镇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电影美学,他当年拿到大钟奖的最佳短片名字就叫《恨》。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24个推荐 粉丝840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