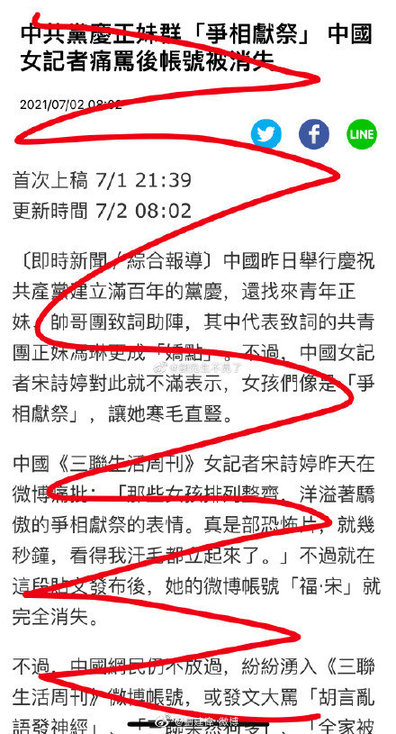突围的《东北虎》和“困在原地的人”
作者:宋诗婷
2021-06-29·阅读时长11分钟

被困住的“东北虎”
《东北虎》这个片名和隐喻从剧本创作之初就想好了。耿军喜欢逛动物园,每次去都转悠很久。“特喜欢上海动物园,干净,没有味儿。”2012年,他去过一次,在虎园里遇到了东北虎,突然入迷,举着机器拍了40多分钟。“那表情里有疲惫、麻木、茫然,很复杂。围栏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高,但它好像放弃挣扎了。”回到家,他把拍来的画面放到电脑上看,越看越觉得,“那眼神儿和我们这些不知道被什么困住的人一模一样的”。那天之后,这只东北虎总浮现在耿军眼前。
也是那一年,当时专做文艺片的天画画天影业公司有一个剧本基金,要求是提交一个故事大纲,还要写出30场戏。“6万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挺大一笔钱。”耿军想抓住机会,他很快就写了大纲和30场戏,“《东北虎》这前30场戏基本没变过”。
故事的源起是一个凛冽的画面。2010年,耿军回家过年。大年初三走在马路上,他远远地看到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在等中巴车。春节期间,公交车少,那人像是等了一阵子,衣领上都落了雪。耿军走近一看,“这不是刚哥吗?”刚哥叫徐刚,至今还是耿军电影的主要演员。那天,刚哥满脸愤怒,要去新华镇一趟,一刻也等不了,因为“家里的狗让人给杀了,要去弄那人”。
一个晚婚晚育的36岁男人,因为孩子要出生,不得不把家里的狼狗送走。自己的家庭成员,一转眼就被人弄死了。那屹立在雪中的孤独且愤怒的中年男人形象和那只东北虎一样,深深地印在了耿军的脑子里。
章宇饰演的徐东原型就是刚哥。徐东和刚哥一样,是鹤岗少有的晚婚晚育的中年人。老婆也正怀孕,狗也得送走,也教过体育,也有份宿管老师的工作,那狗也被人吃了。他要复仇的愤怒撬动了《东北虎》的人物和故事。
比刚哥经历更丰富的是,徐东还有个小情人,那个每天找他帮忙卖诗集的朋友罗尔克存在感也很强。罗尔克的原型是耿军的小学同学张稀稀。当年,张稀稀比耿军才华外露。他读的是清华美术学院的专升本,整天和文艺青年、诗人混在一起,还没毕业,学费就花完了。后来,精神的困惑和生活的窘境让他患上抑郁症,不得不回到鹤岗,找份学校里的安稳工作。再后来,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彻底无法工作了。被精神疾病困在家里的张稀稀依然写诗,写出的词句和生病前大不相同了。
除了每年回家的耿军,几乎没人登门找张稀稀。谁会主动去找一个精神病人呢?但耿军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没暴力倾向,最多就像电影里一样,掐你的脸。”一开始,耿军想找张稀稀来演罗尔克,也在现场试了,“但他待不住,人多了就紧张”。耿军不得不再请自己的御用演员刚哥出场,扛下这个重要角色。
马千里那角色是顺着徐东摸来的。当年,刚哥复仇的后续是,他找到了中间人,商量了一个合适的价码,用金钱摆平了那桩与狗有关的命案。耿军喜欢小动物,人也敏感,他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事,才能对一只朋友托付来的狗下手?
“马千里就是在这样的疑问下创造出来的人物。”耿军说,那是在失落的东北常能见到的一种人,什么火干什么,发过财,也带亲戚朋友赚到过钱。那年代,赚到钱就威风,出手也阔绰。那个破败的农房里有他全部的过去,水泥搅拌机是曾经赚钱的工具,那辆破奔驰车,房间里的马桶、雀巢大杯子,脖子上小拇指粗的金链子……都是他辉煌的过去。而被砸破的窗户、简陋的炕桌、散装白酒和整个院子的凋零就是马千里的当下,也是工业和能源浪潮退去后,鹤岗人的当下。
耿军是1976年生人,这几年,身边的朋友都步入中年。有人出轨,差点被老婆砍了,朋友跑去搭救时,男人家里的剪刀、叉子、菜刀都被他扔到了窗外。有人要教训打麻将被传风言风语的老婆,结果反被愤怒的老婆打了一顿。东北人的不幸婚姻里总充满荒诞和暴力,还有一个被神化或妖魔化了的硬朗女人。
马丽饰演的美玲就是这么来的,她是徐东“中年危机”里的情感危机。耿军不喜欢外化的暴力,他想把这两人的婚姻写成恐怖片,“是智慧上的暴力”。女人的“智慧”体现在透过两根头发识破出轨的老公,“暴力”集中在两场吃饭的戏上。“坚强约等于狠。”美玲用这句干净利落的台词支撑她怀着孕到处捉奸的神经。
“一个小心翼翼的好人,在自己和别人的错误里挣扎徘徊。”这是电影里徐东的困境。鹤岗,这座东北小城被时代甩下了,连带这一群人也被甩下了。他憎恨马千里,也被情人和妻子恨着;他原谅了杀狗的人,自己的出轨也被妻子包容。这是一个不得志的中年男人混沌生活的两面。
同样是中年男人的耿军理解徐东,但也没替他辩解。“是宽容的力量大,还是仇恨的力量大?是让自己凶狠起来,还是柔软起来?我至今没有答案。”耿军说,这电影里每个人的处境都有他的自我投射,只是被打散了,不像曾经的作品那样显而易见。

一堆儿蘑菇
对耿军来说,写剧本的过程就是唤醒自己沉睡记忆的过程。
一开场,徐东和情人的调情方式是互相磕脑奔儿(额头),亲昵中又带点野蛮,那是耿军小时候常玩的游戏。待着无聊,就嗑瓜子,光嗑也没劲,就猜个单双数。玩儿得刺激点,输的人要被扇耳光或者弹脑壳,玩着玩着就急了眼。这是东北的冬天特有的消遣。奶油蛋糕,一口咬下去真香,吃多了却起腻。每个生日,它常和黄瓜炒鸡蛋、蒜苗炒肉同时出现,中西合璧,缺了谁都不行。也不知怎么的,很多东北糙汉都嗜甜,大白兔奶糖和不老林总揣在兜里,反差,但不萌。
耿军对冻梨和冻柿子有感情。小时候,这两样东西一起被放在搪瓷盆里,再倒上水,搁在平房外面。冬天冷,搪瓷盆里的水很快就结了一层冰。黑黢黢的梨,橙黄橙黄的柿子,可好看了。小孩蹲在盆边,手快的一把把冰敲碎,捡个最大的吃,酸酸甜甜,好吃。
《东北虎》一开场,章宇饰演的徐东坐在一辆挖掘机里敲冻柿子,车窗外是鹤岗仅存的一处露天煤矿。这处时代的伤疤和鹤岗的遗产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耿军的电影里。车里,冻柿子裂了个口儿,徐东看似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
《东北虎》的剧本放了好几年,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钱拍摄。那几年正是华语电影市场势头好的年景,也有影视公司看上这个杀狗追凶的故事,找耿军谈合作。“都问能不能把打斗和追车的戏多加点,更外化、更商业一点。”一开始,耿军觉得是机会,就和编剧试着改了一阵子,越改越不对劲儿,“味道全变了”。
和前作《轻松+愉快》、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相比,《东北虎》对鹤岗大环境的关照弱化了。这一次,耿军明显减少了全景和远景画面,大环境的萧条也被精心设计的美术色系和构图建构得不那么原始了。
他把镜头拉得更近,更贴近人物和他们的情绪。“用事件和戏剧冲突写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充分地写一个事件,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我更关心在这个事件里,被困在环境里的这群人是什么心理和状态。”耿军说,“《东北虎》的风格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点表现主义的东西。”
徐东是个有弱点的好人,人善良,也仗义,讲究的是江湖规则。马千里在生意场上走了一遭,遵纪守法不一定,但办事讲个规则,尤其是对自己有用的规则。马千里把和徐东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在公安局门口。在法律秩序的监督下,用江湖秩序解决问题,这是推进《东北虎》矛盾产生和发展的价值观分歧,也是耿军的幽默。不能说《东北虎》是喜剧,但电影里充斥着耿军惯有的黑色幽默。
《东北虎》是耿军第一部即将走进院线和大众正式见面的电影,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里启用职业演员。
章宇是贵州人,一头扎进东北。要融在常年演耿军戏的非职业演员中,不是件容易的事。电影里,他也偶尔说几句口音挺重的东北话,但多数时候,台词还是普通话。刚开始做电影时,耿军就抛弃了抖机灵式的东北话,他对语言的节奏更感兴趣。
《东北虎》在鹤岗最冷的时候开机,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外景拍上两条,演员就得躲进边上的小卖部里暖和一会儿。一天的外景戏拍完,耿军就回去给大家送白酒,“尤其是摄影组的兄弟”。下午4点多,天黑了,剧组回到酒店,大家先坐下来喝几口。不喝酒的也得来点儿,不然一时半会儿暖和不过来。
鹤岗纬度高,冬天下午不到4点太阳就落山。人长时间处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裹在厚重的衣服里,语言和思维都像是被冻住了,一切都有点缓慢。这缓慢有点丧,突然爆发又极有力量,那是《东北虎》里语言和人物性格的精髓。
在现场拍戏时,耿军尤为看中演员语言和动作的节奏。有时,马丽演完一场戏用了16秒,耿军会把她叫过来,悄悄说:“13秒最准确。”章宇回去再演两遍,节奏最好的那条果然是13秒。“要么怎么说电影叫雕刻时光呢?”耿军借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话说。
在东北的冬天,只要是个活物,走在街上都冒着蒸汽。猫猫狗狗的鼻子都湿乎乎的,让人想摸一把。人也一样,一进了屋,蒸汽化成水,也湿乎乎的。“就像地上的蘑菇,湿润的,圆乎乎的,特可爱、特憨。每个蘑菇看起来都差不多,一细看,都不一样。”耿军希望,他电影里的角色都是湿润的蘑菇,有点憨,像从卡通片里走出来的,“即便是坏人,也不过是株毒蘑菇,也挺可爱的”。
电影筹备和拍摄的那段日子,剧组的每场酒局章宇都没落下。这是性情使然,也是他走进人物和鹤岗的办法。耿军还记得,主创喝的第一顿酒,章宇很谦虚,跟刚哥、勇哥、宝鹤这些鹤岗土著说:“我这块肉就交给你们了,哥儿几个帮帮我。”那之后,章宇就每天和这帮人混在一起,戏里穿的衣服也不脱了。在人堆儿和酒堆儿里泡了一阵子后,整个脸都浮肿了,锐气弱了,中年人的疲惫感就有了。
马丽也收起了她最被大众认可的喜剧演法,变得缓慢、冷静,幽默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像极了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里的女人。
电影快拍完时,章宇跑到耿军身边问:“导演,我是蘑菇了?”耿军答:“对,你和他们一样,你们都是一堆儿里的蘑菇啦。”守着这堆儿蘑菇,耿军特高兴。

从鹤岗出发
电影里,徐东和美玲的房子是剧组在一栋干部家属楼里租来的。顶层,房间挺大,100多平方米。美术组重新粉刷布置了一通,拍完又给变回了原样。“失策了,不如买下来,也就8万块钱。”耿军调侃鹤岗的房价。
2018年底,《东北虎》剧组到鹤岗勘景,美术师随手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广告栏里的卖房广告。电影杀青时,这勘景照片又被他随手发在了朋友圈。美术师的好友里有个媒体人看到了,瞬间嗅到了“新闻”的气味。就这样,全国媒体蜂拥而至,“鹤岗房价500元/平方米”的讨论在网上大火了一把,这是鹤岗难得的“高光”时刻,尽管说不上好坏。
“据说,几个月的时间,鹤岗卖给外地人2000多套房子。”耿军说,爆出来的都是棚户区改造楼,政府不太愿意炒作这事,房管部门的LED滚动屏上打出的都是中高端商业地产的房价,三四千元一平方米,显得体面不少。
房价每平方米500块的鹤岗像是被经济社会抛弃了,但它在努力追赶,建了繁华的时代广场,有综合商圈,两家电影院,其中一家还叫“戛纳”。但这些都比不上市人民医院的人头攒动,那是“全鹤岗营业额最高的地方”。
总有人问,拍了那么多鹤岗,还能拍下去吗?耿军可不这么觉得。“能拍的还多着呢,戛纳和时代广场可能就出现在未来的电影里。”耿军说,每年回家过年,跟老家的朋友保持联系,那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来源。
疫情期间,耿军在老家鹤岗困了四五个月。很多年没这么长时间和父母待在一起了,“差点处出感情”。冬天的鹤岗暖气烧得狠,屋里二十五六摄氏度,待久了,人燥热。每天的《新闻联播》像是放风哨,音乐一响,耿军就出门遛弯儿。鹤岗不大,绕着内环走上一圈,也不过消耗两小时。走热了,就再干掉两三瓶啤酒,这祛火降温的法子被耿军父母视作“酗酒”。
早几年,一回鹤岗,耿军就和固定的那拨人厮混,不太愿意凑同学聚会的热闹。大家年龄差不多,但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不同,聊起天来像两代人。这两年,耿军变了,同学也变了。“进入了一种互不羡慕、互不干涉的状态,愤怒和愁眉苦脸的气氛都过去了。”耿军说,有人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打牌,人生到了中场,有点尘埃落定的意思,反而能坐下来聊聊天了。
过去这些年,学者、媒体、作家、影视圈都想探究东北的衰败,那里有经济规律、社会学价值,还有特有的颓丧美学。但所有目光都很难聚焦,除了情绪和状态,很难找到研究和讲述的抓手。“所以电影是直接的,表达情绪,展现状态,这是艺术能做到的。”耿军说。
他不想把自己和自己故事里的小人物放入某种历史和文化框架。“我只认我真正能感受到的情感和情绪。走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身边人的气息、语言和状态,那些东西是我在乎的;我爸、我妈,我的这帮同学是个什么样,这对我是有意义的。至于那些描述东北的大词儿、小词儿,我都不在乎。”
耿军电影里那些演员曾经是鹤岗最普通的年轻人,现在是鹤岗最普通的中年人。不拍耿军的戏时,小二还待在家里,刚哥还在学校做宿管老师,勇哥在残联工作,袁利国在双鸭山的一所中学里教音乐,宝鹤在鹤岗开了个公务员培训学校,疫情期间过得不容易。随着耿军的电影越拍越好,他们在各自的地盘都更有面子了,跟领导请假也有了交代。这大概是作品拿到更多奖项,尤其是拿到上海电影节最佳影片后最务实的福利之一。
《东北虎》的结尾独白也是耿军从记忆中打捞出来的。19岁时的徐东和动物园里那只19岁的东北虎,勾连了耿军的少年时代——小时候,他总生病,一病就发烧。轻一点的,来一串冰糖葫芦或者山楂罐头,再吃一盆鸡蛋羹就能好;重一点的,就得去医院打点滴;最重的时候,耿军和电影里的徐东一样,得靠妈妈连背带扛地送去医院。
绝望时,他们都怕自己会死掉。徐东的妈妈对他说:“未来可好了,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未来可有意思了。”耿军的妈妈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徐东和耿军站在“未来”,回忆过去对当下的憧憬,其中自有暖意。但年根底下的鹤岗实在太冷了,这暖流凝固在电影的现实里。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838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