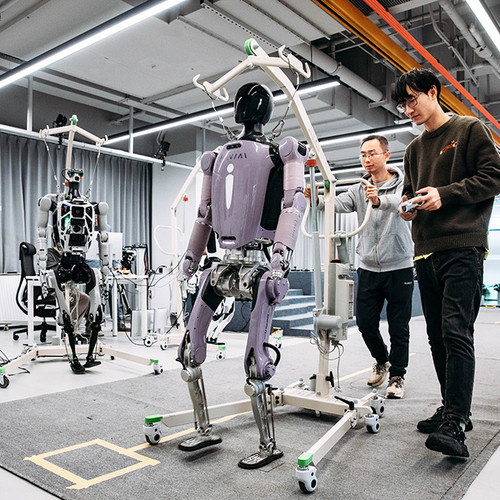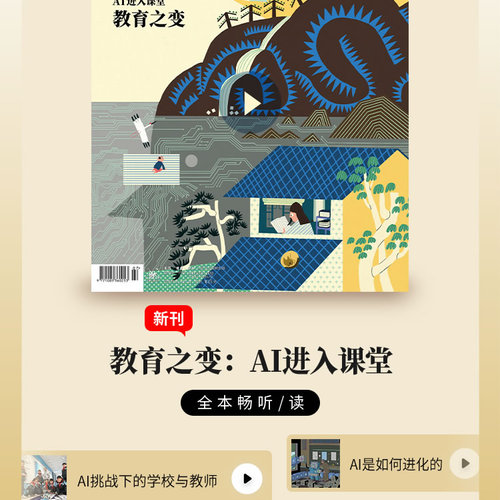景德镇访窑记:一座烈火炼造的城市
作者:张从志
02-18·阅读时长16分钟

御窑:碎瓷、碎砖里的历史
我问过的人都说,到景德镇,首先要去的就是御窑。作为一个专门服务皇家的机构,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创立到清末停烧的500多年时间里,御窑将中国手工制瓷的历史推向了巅峰。这里出产的瓷器,如今也成为全球博物馆、拍卖行趋之若鹜的对象。我们在景德镇的踏访就从这里开始。
御窑在景德镇老城的中心位置,遗址所处的地方是一座小山丘,当地人称为珠山。珠山上修了一座龙珠阁,爬上去,就能俯瞰老城的全貌。我和白光华约在御窑的东门见面,一般游客不太走这道门。他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向我们招手。白光华今年63岁,穿着一件藏青色扣衫,头戴棕色的前进帽,脖上系一条围巾。他是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文化研究者,也参与了御窑多次的考古工作,外地朋友来景德镇,他也经常带他们到御窑转转。

从东门进来,首先要穿过一片厂区,这里是原来的十大瓷厂之一的建国瓷厂,现在已经成为陶阳里历史旅游区的一部分,厂房被改造成不同的空间,里面引入了一些餐厅、咖啡馆和市集。穿过厂区,白光华带我拐进了一条很窄的弄堂,绕了几下后,从一个侧门进入御窑厂,首先碰到的就是一座十分当代的建筑——御窑博物馆。几个巨大的红砖拱形建筑在地上排列开来,在它对面的坡上,就是龙珠阁。
2021年落成的御窑博物馆如今已是景德镇的网红打卡地,即使春节后人流下降,这里依然有不少游客在拍照。博物馆内最有名的展品是一只被网友称作“岁岁鸭”的“鸭子”。这只“鸭子”官方名称是“素三彩鸭形香薰”,诞生于明成化年间,但因未能通过御窑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击碎后埋入地下,并无其他存品传世。现在的展品是修复人员从考古发掘出的60多片碎瓷中挑选出来并修复完成的。


走进御窑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展品,从小件的茶碗杯盏到大型龙缸,都是这样的碎瓷修复品。这与御窑厂当初特殊的管理制度有关——这里生产的瓷器专供皇家,不符合标准的瓷器要敲碎后就地掩埋,严禁流入民间。上世纪80年代初,白光华刚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御窑里面还是市政府的驻地,大门前的马路经常在挖管道、修市政工程时挖出碎瓷片,上面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研究所的人经常要去现场调查。随着发掘出的东西越来越多,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2002年底,景德镇市政府办公场所迁离御窑遗址区域,并将原政府办公大楼拆除,开始全面启动御窑遗址的保护工作。从那时至今,御窑已经挖掘出上百吨,近2000万片碎瓷片,很多瓷片的出土,填补了国内陶瓷史的空白。

离开御窑博物馆,从珠山脚下绕到南边,我们向御窑厂的正大门走去,约两三百米,来到一口古井面前。白光华说,这口古井在明清时就有记载,一直保存至今,成为人们定位御窑厂的一处标志。在古井的右手边是一处作坊遗址,曾是御窑厂工匠拉坯利坯的车间。作坊如今只遗留下矮矮的一截墙根,可以看出墙体是用废弃的破匣钵、拆下来的窑砖砌筑的,还有的是用大块的鹅卵石堆成的。墙与墙之间的距离也很近,说明作坊里空间非常逼仄。站在遗址前面,白光华突然发问道:“看到这些,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如果跟你在故宫里看到的那些瓷器联系起来,你是什么想法?”他自顾自地讲起,过去有领导到景德镇履职,就以为御窑厂过去的建筑是很恢弘、气派的,毕竟是皇家机构,结果一看,这里挖出来的遗址和周围的民窑别无二致。“多么粗蛮,多么简陋,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居然做出了那么精美的瓷器。”
白光华喜欢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御窑以及自己从小生长的景德镇。他告诉我,景德镇人的家里过去很难找到一套完整的餐具,即使有也是各个厂家的杂牌,而且是有缺陷、有瑕疵的。一是好东西是要拿去卖钱的,二是我们做瓷器的对用什么见惯不怪。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前身)建馆的时候,也找不到一套像样的瓷器来展示。“我们有的只是一些墓葬里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品质不算很好。你现在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看到的所谓镇馆之宝都是30年前从别处购买来的。”

从作坊遗址向对面的坡上走去,上一段台阶,看到的是成片的窑炉遗址。这些窑炉规模都不大,有明代的葫芦窑,更多的是后来发明的蛋形窑和马蹄窑,这些窑炉的名字都是根据其形状命名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烧制需求和窑炉营造技艺。“比如蛋形窑是从北方引进的,明代原来用的葫芦窑比较大,改成蛋形窑后,体积缩小,更好控制温度,还可以分类烧制,出品也更加稳定。”白光华告诉我,御窑厂最多时有58座窑炉,现在挖掘出来的有十六七座,最古老的窑址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在现在的御窑厂北侧。
除了这些作坊车间,御窑厂内原来还有衙署。根据历史记载,衙署建筑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典雅。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创办御器厂,最早是州府一级的官员负责,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是派皇宫里的宦官来管理,级别比景德镇所在州府还高。而明代实行的是世代承袭的匠籍制度,工匠属于贱民,到御窑厂工作的工匠相当于服徭役,生存环境自然恶劣。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童宾的御窑厂工匠就是在厂内某一处窑炉投身自焚,以反抗当时主管御窑厂的宦官对工匠们的压迫。他投炉后,原来迟迟烧造不出的大龙缸也终于成功。童宾从此被景德镇人奉为“窑神”,后来御窑厂也特地为他修了一座庙,叫风火仙师庙。
从御窑厂的西门出去,我们扎进了景德镇老城的街巷里弄。这里房屋密集,巷子窄而深,穿行其中,常常不经意就碰到一处旧窑,有的只剩下遗迹,有的经过修葺后,恢复了往日的规模。走在巷子里,我们脚踩的地面、旁边的墙上都能看到很多玻璃化的灰砖和红砖,这些都是过去留下的窑砖。在老城里,这样的窑砖建筑随处可见。白光华说,一是因为清代以后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御窑厂会把一部分的瓷坯委托给民间的窑口烧炼;再加上晚明以后大量的外销瓷器,烧造需求扩大,窑业规模也进一步增长。在当时的景德镇城区,土地资源十分紧张,所以有些窑就做得很大,甚至有两三层楼高,这些窑每年至少要大修一次,不然就会有坍塌的风险,而拆下来的那些断掉的、变形的、不规整的窑砖和废弃的匣钵、窑渣就常常被用来修路、修下水道或者盖房子。这使得景德镇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江南重镇的建筑样式,也奠定了这座手工业城市的色调。

镇窑:手工业的极致效率追求
站在龙珠阁上向西望去,将今天的景德镇一分为二的昌江比我想象的要局促得多,它没有大江大河的那种磅礴气势,而是一条受到山势束缚的河流,河面并不宽阔,两岸的建筑紧紧地挤在一起。元宵节前后,南方的枯水季尚未结束,江水不疾不缓地自北向南流去,最终汇入鄱阳湖。
1712年9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在一封寄往欧洲的信件中这样描述道:“当人们从某个峡谷进入港湾时,呈现在眼前的是这样的景象:各处升腾起的火焰和烟云首先可让人看到景德镇的纵深范围和轮廓。入夜,真好像看到了一个到处着火的大城市,或是一个有许多通风口的大火炉。”这时候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陶瓷的生产中心,在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刺激下,变成一座“雷电之城”,吸引了殷弘绪这样的欧洲人的目光。他在景德镇住了7年,除了传教,也肩负着替欧洲世界刺探景德镇瓷业秘密的任务。在寄往欧洲的信件里,殷弘绪花了大量的篇幅,详细报告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历史以及生产流程、原材料、工艺等技术细节,试图帮助欧洲仿制出这种精美、昂贵的瓷器。
长期研究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在此定居多年的章武告诉我,古代的景德镇就相当于今天的东莞,要把它放到全球化的视角下去理解。这背后有两件事情推动了景德镇的陶瓷走向世界:一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二是鄱阳湖的扩张,打通了昌江的水运,通过水陆交通把景瓷运往广州,然后装船前往欧洲。在御窑厂,我们看不到这种市场驱动下的瓷业盛况,章武建议我去古窑民俗博览区找周荣林,他是景德镇古窑文化研究院院长。

古窑民俗博览区是景德镇唯一的5A景区,位于昌江区枫树山蟠龙岗,从御窑开车过去,要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是元宵节,下着微雨,周荣林在电话里告诉我,古窑这天正好要举行窑神祭祀仪式,还有烧窑、开窑等活动。我们上午9点到的时候,景区里还没多少游客。10点左右,祭窑神仪式在童宾广场上开始,担任主祭的是景区一帮老窑工,主持仪式的是周荣林。他从事传统窑口、民俗的研究已有三四十年。随着仪式的进行,现场围着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祭神之后,是最让人期待的开窑——这种现场即使在景德镇也不多见了。
这天要开的是御窑“六式窑”中的风火窑。周荣林介绍,御窑的“六式窑”包括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和匣窑。“青窑一般是烧小件的青花瓷;龙缸窑专门烧龙缸;风火窑,古人认为烧窑要靠风靠火,烧综合性的大件;色窑烧颜色釉;爁熿窑烧低温颜色釉;匣窑是烧匣钵的。”2013年至2014年,古窑民俗博览区陆续复烧了“六式窑”,重现了明清御窑的完整体系。周荣林把在景德镇有名的柴窑把桩师傅胡家旺请来,给今天的开窑仪式坐镇。胡师傅今年80多岁,身体健壮,如今依然有很多想恢复传统柴窑的人会来请他。他在古窑也干过几年的把桩师傅,全程参与了各种窑型的复建复烧工作。
随着开窑师傅的一声“开窑”,窑洞的封墙被凿开,窑工进到里面,开始一件件往外传递匣钵,外面的师傅接过匣钵,打开后,里面的瓷器露出真容。开窑的过程有点像开盲盒,打开匣钵之前,没人知道里面的瓷器烧制得怎么样、成色如何。所以古代的窑工在开窑之前都要祭窑神,祈求保佑。随着一件件瓷器被师傅双手举向头顶,围观的游客们一个个伸长了脖颈,踮起脚尖,想要一堵其风采。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景德镇城市改造的推进,很多过去留下的柴窑都面临被拆的命运。市里决定找个地方把一些典型的柴窑和作坊集中保护起来,最后选中了枫树山蟠龙岗。从城里拆下来的材料被拖到这里,开始复建窑房、作坊等。此外,蟠龙岗还组建起一个古窑瓷厂,接收了200多名做传统瓷器的手工艺人。
1988年,周荣林被调入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做馆长,并兼任古窑瓷厂厂长,直到2008年退休。他告诉我,他在博物馆当馆长的时候做过景德镇陶瓷发展史基本陈列,里面也有窑炉的陈列,但当时就是在展厅里用红砖砌了一个模型,“只能看,不用烧”。“我们提出要做一座活的博物馆,有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进行生产性保护,比如窑炉营造、材料烧炼、手工成型等等。如果没有真实生产,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视频上,技艺就传承不下来。”退休后,周荣林担任了景德镇历代瓷窑复烧专家顾问团团长,开始推动传统柴窑的复建复烧。
在古窑民俗博览区,最具历史价值的是清代镇窑,其始建于乾隆年间,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窑是用拆下来的材料复建的,占地有将近1000平方米,呈长方体,屋顶是斜的,有几叠,铺的都是青瓦,偏后的位置有一根红砖砌的烟囱高高矗立着,显得十分气派。镇窑的窑炉属于蛋形窑,因其形似鸭蛋。窑房里分成上下两层,下层用来堆放匣钵、瓷坯,还放着烧窑师傅们休息喝茶时的桌椅,二楼通常用来储存木柴,过去也会做一大通铺,是窑工们睡觉的地方。
2008年,古窑民俗博览区改制,由民营企业接手运营。2009年,景区里的清代镇窑实现了第一次复烧,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柴烧瓷窑。这次复烧,用了40吨木柴,放进了300多担(一担通常是50公斤)瓷坯,出产了2万多件瓷器。据说,总花费高达600多万元。
如果说御窑代表的是审美最大化的工艺追求,那么以镇窑为代表的民窑,则是景德镇手工制瓷史上对效率极致追求的产物。在清代,景瓷生产规模达至历史顶峰的过程中,镇窑诞生,并围绕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组织体系。章武对镇窑有过专门研究,他告诉我,一个镇窑通常会配套24个生产不同工艺品类的小作坊。“因为古人把镇窑里面虚拟地划分成24个不同的温度区,前后温差最高能相差300多摄氏度。每个温度区烧的泥釉配方是不一样的。圆器11业、琢器17业,几乎每一个行当都能在镇窑里找到一个对应的窑位。”章武说,这些窑位从前到后,从一路、三路、四路一直到四十路,一次烧窑,可同时烧制几十种不同的产品。过去的作坊主都是提前买定窑位的,各家的匣钵、瓷坯什么时候进场、摆在哪里,涉及一套复杂的组织调度。而且,出窑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窑工不能等窑内温度完全降下来便要进去作业,紧接着就要装窑,身上经常被掉下来的窑渣烫出疤痕。
古窑民俗博览区的清代镇窑过去几十年只复烧过三次,就是因为成本上确实很高,体系太复杂,在今天操作起来反而不易。“在过去,一个窑一般一个月要烧四五次,周转越快,成本就越低,产量越高。可以说,景德镇的瓷业历史延续千年,跟窑炉的不断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周荣林说。

从隧道窑到梭式窑:一家国营瓷厂的自救之路
镇窑这种传统的柴窑,生命周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后来,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景德镇组建起了“十大瓷厂”,分别生产不同的瓷器,柴窑也逐渐被煤窑、气窑所取代。景德镇的陶瓷生产逐渐从手工业时代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传统技艺和经验被工业流水线上的科学生产所取代,一众科研院所在景德镇成立。在今天的景德镇,很多瓷厂的老厂房里依然能找到这些巨大的工业窑炉,它们也被称为隧道窑,有的已经像陶溪川一样被改造为工业遗产旅游点,有的仍然废弃在那里,无人问津。
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对景德镇人来说是一段十分动荡、痛苦的经历。1995年,十大瓷厂全部关停,数十万瓷业工人下岗,自谋生路。章武那时候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来景德镇,对当地社会的失序状态记忆深刻,街头上开始出现黄赌毒现象。但这段痛苦的历史,也给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创立于1956年的景德镇雕塑瓷厂是这种转变的代表,在陶溪川兴起之前,这里也是年轻人常去的地方,特别是那里的创意市集,十多年前吸引了国内外很多艺术家的驻留,在艺术圈名气很大。雕塑瓷厂在景德镇珠山区新厂东路上,我去过三次,最后一次是个雨天,门口的摊位前挤了不少躲雨的人。许绍文在雕塑瓷厂的牌坊下面等我们,一见面,雨点大了起来,他带着我们赶紧躲进了旁边的明清园。
明清园是雕塑瓷厂1992年修建的一处仿古园林,里面有亭台楼阁,现在很多都被开辟成了民宿和咖啡馆,也有卖瓷器的。许绍文是雕塑瓷厂的前厂长,自从2012年卸任后,他也很多年没有回这里了。在一处亭子前,我们停下脚步,许绍文身材中等,穿着体面,笔直地站着。他介绍说,明清园是当时的老厂长刘远长主持修建的。当时,他们在整个景德镇乃至江西省,第一个提出了发展工业旅游的口号。厂里找人搜集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古建构件,比如门雕、房架等,建成了这个有徽派风格的古典园林。后来,明清园吸引来一些国内旅行团,还有港澳台同胞前来观光。景德镇不少人都认为,陶瓷厂搞文旅的模式,就是从雕塑瓷厂的明清园开启的。
章武告诉我,雕塑瓷厂当时做的另一件事情,对后来的景德镇影响也很大。那就是1991年,在刘远长的推动下,雕塑瓷厂从澳大利亚引进了景德镇第一台燃气梭式窑。和过去的隧道窑相比,梭式窑更加小巧灵活,可以像抽屉一样,每次只烧一小批。许绍文说,十大瓷厂解体后,很多职工在厂里搞起了小作坊,那时候的小规模生产主要靠的是这种梭式窑。而最早引进梭式窑的雕塑瓷厂,也有了“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到上世纪90年代,很多瓷厂已经举步维艰的时候,雕塑瓷厂还在努力维持经营,寻找转型之路。

许绍文就是在明清园修建的那一年,从厂办学校调进工厂里的。他之前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这原本是老厂长刘远长制定的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规划了20多个指标,最后就进来了两个人,许绍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此在雕塑瓷厂待了下来,最早是做销售,到全国各地去推销瓷器。雕塑瓷厂主要生产传统的雕塑瓷,题材也是传统的神话人物和花卉植物等,当时第一批通过市场经济赚了钱的人,对这些传统的东西还感兴趣,所以雕塑瓷还有市场。不过,这些订单远远支撑不起一个上千人的大厂。
许绍文后来还给一个英国人做过三年的花盆。那是1993年,英国人拿着一个瓷坯跑到雕塑瓷厂请人帮他烧一下,烧完后,他问刘厂长能不能做花盆。刘远长组织了几个人,把他要的花盆样品都做了出来,最终许绍文和英国人把单子谈下来了,价格还不错。但雕塑瓷厂不生产花盆,工人们也不愿意做。许绍文只好跑到市里面做雕印的店,告诉来买印子的工人:“你们想挣钱吗?想挣钱明天早上8点到雕塑瓷厂后面,我在那里等你们。”第二天,他就招到了108个工人,都是外厂的。从1993年做到1996年,他们给英国出口了23个货柜,纯利润200多万元。

1995年,十大瓷厂开始改制,市里给的八字方针是“关停并转,逐步爆破”。生产班子化整为零,职工各谋生路,厂子也名存实亡了,只保留了一些必要的行政部门维持运转。2003年,许绍文当了厂长。他说自己当时实在不想接手这个摊子,厂子虽然不生产了,但还有700个退休职工,每年还要凑十多万元的社保金上缴。当时厂房都租给工人做小作坊,租金却很难收上来,有的是不愿意交,有的是实在困难。有一次许绍文去一个作坊里收租金,作坊主连一个月150块钱的租金都交不起,儿子考上了大学,因为没钱供,只能在家里帮忙。
十大瓷厂的解体,在章武看来,让景德镇的瓷业从工业化时代一下退回到了农副业时代,生产形态从过去的集中又回到了分散。后来,佛山、潮汕、德化等地的陶瓷产业崛起,对景德镇的家庭作坊再一次造成冲击,很多人选择了南下,给工厂打工。还有一部分人则留下来,回到了传统制瓷的轨道上,这也给民间业态的生长留下了空间。
2005年,经过一个中间人的介绍,许绍文和乐天陶社的创始人郑祎认识。郑祎那时候在三宝村带着一帮外国人做陶瓷,还在景德镇到处转悠,对他们包吃包住,向他们收费。许绍文觉得这种模式很不错,正是他们要学习的。两人谈过一回后,乐天陶社把雕塑瓷厂原来的展览室和行政楼都租了下来,改造一番后,开始在那里做国外艺术家驻场,后来还有了创意市集。
许绍文说,自己当时最看好的是乐天陶社每周五下午举办的那堂免费讲座。“那时候还有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来讲,他们都不保守,自己创作时有什么冲动、来自哪里、用的什么手法,全部拿出来讲给大家听。我们那时候本地陶瓷行业已经不行了,做不过别人,又缺设计,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让大家的想法形成碰撞。”

随后几年,在乐天陶社的运营下,雕塑瓷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陶艺爱好者。不过,这个过程中,厂里也经常发生各种矛盾。有一年刮大风,把路边的三棵法国梧桐树吹倒了,幸好没有砸到人。许绍文就组织人手里把厂里20多米高的树全部削平只留5米。有个外国艺术家对此很不满,在路上指着许绍文问:“你为什么要砍树。”许绍文说,“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明年春天你来看。”结果到了第二天春天树都开始抽枝,夏天绿荫如盖了。“我说我们厂的这些树几十年没有修剪,根底都很浅,修剪之后,反而利于生长。”还有一次,一个北京来的艺术家做了一批瓷器,里面有一些作品对历史人物不敬,被工厂保卫科的人拦下来,双方争吵之下,把许绍文给惊动了。“我去看了一下,大部分东西都放走了,就把里面最难看的两个扣了下来。”这样一来二去,许绍文和这帮艺术家也混熟了。
2012年,许绍文卸任雕塑瓷厂厂长,去了当时正在启动开发的陶溪川。如今,雕塑瓷厂看起来也生机勃勃,主路两旁挤满了各种摊位,厂房里还引进各种咖啡馆、陶艺体验馆,有很多年轻人在里面做陶艺。但变化也在发生。郑祎已经把乐天陶社的市集搬离了雕塑瓷厂,她不喜欢现在的小商品生态,去了一个更加偏僻的地方。一个在雕塑瓷厂干了一辈子的传统艺人也告诉我,这两年房租上涨太快,而雕塑瓷的市场收缩得厉害,也感到无力支撑,正在做下一步的计划。
文章作者


张从志
发表文章66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309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