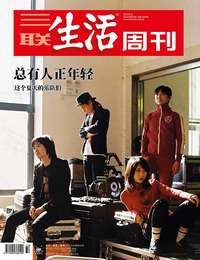现场,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宋诗婷
2019-08-07·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658个字,产生1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 IC fotoe供图)
七八年前,我在MAO livehouse看过一场演出,那会儿,MAO还在鼓楼东大街111号。
当天的主角是一位已经解散了的乐队的主唱,后来,他单飞,娶了个做模特的老婆。整场演出都在文明、友爱、矜持的氛围下进行,唱到后半场,主唱心疼歌迷,让大家坐在地上歇着听。歌迷都很听话,除了我们这些站在后排的,大多乖乖坐下。当时,我正站在门口,眼看着一个披着长发,大花臂,穿着马丁靴的男人晃进来。他一看这现场,立马急了:“都给我站起来!这他妈是MAO!”
这一吼,可把歌迷吓坏了,主唱也尴尬了。蒙了的歌迷稀稀拉拉地站起来,主唱干脆找个台阶下:“那大家都站起来吧。”现场恢复了MAO的“秩序”,男人勉强满意,转身又晃了出去。
我把这个多年前看演出的经历讲给迷笛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迷笛音乐节创始人的张帆听。“有可能,很有可能。”张帆笑坏了。
这让他想起2003年的迷笛音乐节。当时,音乐节已经办了四届,都在迷笛学校内,那年,受到各种鼓励,张帆决定让迷笛走出树村,走向人民群众。几经周折后,最终地点定在了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切都还算顺利,但在站着看,还是坐着看这件事上,张帆和有关部门产生了分歧。“坐着看不利于疏散,消防、撤离这些安全问题都有隐患。”张帆向来擅长进入对方的语境来协调问题,这也是迷笛音乐节和迷笛学校能经营这么多年的重要原因。

迷笛音乐节现场的露营区(祝若愚 摄)
如此坚持的深层原因是,任何形式的把人固定在某个位置上都是种束缚,“你的行为被限制,不能去POGO,不能跳水,不能自由地穿梭、交流、拥抱。只有身体先行动了,大脑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身体,才能自由地表达欲望。”张帆说,迷笛从一开始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营造一个乌托邦式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人们可以进入同一个语境,有生活中缺少的自由状态,音乐很重要,但那只是构建环境的大背景,更重要的是,“你得是一个特别洒脱的年轻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疯狂,躁,这是迷笛音乐节演出和迷笛观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从一开始就定下的基调”。2000年,在迷笛学校老校区的破旧礼堂里,全国第一个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诞生了。说是礼堂,其实是间500多平方米的废弃厂房。考虑到要让观众离乐手尽量近,方便感染气氛、跳水和POGO,学校在礼堂里搭了个不太高的1.2米台子,就算是演出舞台了。音响系统都是从当时的麒麟童文化借的,音箱都不是同一个牌子的,随便拼凑在一起,“声儿够大了就行。”
参加演出的乐队大多是迷笛学校的在校生,或已经离校组乐队的校友,比如痛苦的信仰、夜叉和舌头。演出那天,位于市郊的迷笛学校礼堂涌进了几百人,还有几百人挤不进去,只得站在门外做旁听生。礼堂的落地窗玻璃已经全部被拆下,这是个相当人性化的举措。操场一角的琴房改成了扎啤供应区,学校预定了大量燕京啤酒,免费提供给当天的观众。负责打啤酒的老师没有经验,拧开啤酒龙头后冲出来的都是泡沫,不一会儿白色泡沫就铺满了琴房。

迷笛学校院长、迷笛音乐节的创始人张帆(骆驼 摄)
去看演出的有在校师生,有诗人、作家、媒体人,还有从没看过演出的工人和农民,有些初来乍到的被前排疯狂甩头和POGO、死墙的架势吓到,一步步往后退,退出核心位置。但只需站在边上看一会儿,很快就会被现场疯狂的气氛感染,怕了的人会重新一步步靠近,最终又消失在狂欢的人群里。
到了第三届迷笛音乐节,迷笛学校已经搬迁,校园里有了一片开阔的场地,音乐节也第一次走向了室外。从各地跑来看演出的人更多了,不仅是北京市内和周边城市,还有人从新疆一路坐火车赶来狂欢。那也是迷笛音乐节开设露营区的起点。当时的学校院子里有很多果树,音乐节一连两天,很多远道而来的人都不回去,台上安静后,台下的人就各显神通了,唱歌、弹琴、喝酒,累了、困了就在果树下睡去。那时,北京还没有雾霾,夜里还看得到天上的星星。
过去这近二十年,迷笛音乐节越做越大,也开到了上海、太湖、山东、深圳等很多地方。2007年,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出现了,随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音乐节都出现了,直到今天,每年全国有上百个不同规模和定位的音乐节。这些音乐节让很多曾经生活艰难,几乎要放弃音乐的乐手们吃饱了饭,甚至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究竟有多少人是去听音乐的?”我问张帆。
“今年的太湖迷笛卖出七千多张通票,这意味着有大几千人都要在迷笛露营。当时,音乐节的露营区架起了四五千个帐篷。英国最大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和丹麦最大的罗斯基勒音乐节每年都有四五万人露营,露营区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有些人根本不去听音乐,他们在帐篷间窜来窜去,自己拉来整车厢的酒,谁在听音乐不重要,大家就是在过一个节日。”张帆回答。
就像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说的,早些年,中国观众看演出和参加音乐节的神经都太紧绷了。最近几年有了好转的迹象。大家“玩起来了”,开始把喝啤酒、看现场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好的音乐节除了音乐本身,能建立怎样的规则,构建怎样的“社会”就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83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