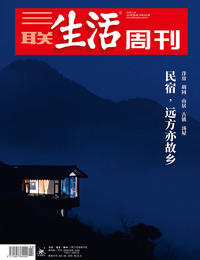民宿之美在于神
作者:徐菁菁
2019-01-09·阅读时长2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3743个字,产生32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远方的诱惑
“我真叫王小花”是我的一位老相识。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朋友圈见证她的壮举:在北京昌平僻远的山谷里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民宿。今年3月份开始,王小花以每天车行八九百公里的效率用3个月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乡野,最终相中了一个全封闭的大院子。“一共400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我只建10个房间。这是一个7米高的大谷仓,我把它劈一半儿,这边儿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餐厅。”她在纸上给我画草图,“剩下的地方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花园。”
设计和建造这个院子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我表达。“如果我说,身处在几百朵藤冰山月季中的感觉很美,你能够体会得到吗?有很多活在我脑海中的美丽的东西,我靠语言你们什么都感受不到,我只有把它创造出来。”王小花想要创造的东西很多。她希望她的庭院像日本园林一样含纳四季之美,又像欧洲花园一样亲切近人。她想让每一个客人有一块私密的小花园,在夏季桑拿天的午夜,全身赤裸地站在那里,仰望漫天星星,让山里的夜风吹过身体,清凉每一个毛孔。她还打算一手拟定主题菜单,规定客人们在她认为最恰当的时间,品尝她亲手烹制的食物。
王小花承认,修建一所这样的民宿,是一场“天真而幼稚”的冒险。前几天北京地区降温,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厨房里冻了一夜的抹布敲在墙壁上如石头一般铿锵作响:“我现在需要重新考虑如何给我的蔬菜保鲜。”这样的“意想不到”每天都在发生。工程远比她想象的浩大。初冬的时候,赶在土地霜冻前,她和伴侣冯先生曾经花了3天时间,耗尽力气种下了80株玉兰。然而,“80棵树,在4000平方米的院子里,就像撒下一把小草”。开工之前,大学商科毕业的她曾经认真为自己的民宿制作了商务模型,但她很快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用。“最简单的例子,从高速公路下来开车到这个院子要走40分钟的山路。所有建筑材料要拉上山,所有建筑垃圾都得运到山下去,这个成本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园子在山上,排污系统怎么办?我一心要做四个私家浴池,需要的热水远超预期,热力循环系统怎么解决?这些都不在我之前的考量中。没有经验,蒙圈儿了。”
即使蒙圈儿,这个冬天,王小花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山谷里。“那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不得不all in(押上全部筹码),你只能all in!”她形容现在的自己,一边为庞大的工程焦虑不已,一边又为创造的可能性兴奋至极。王小花之前做连锁餐饮的运营,深深地纠缠于简单的商业模型。“模型是可复制的,而团队的终极目标是执行可复制。这整个过程真的富有创造性和乐趣吗?”但民宿不一样。“如果把4000平方米面积切分成80×80的小块,这6400块,可以随着我——园子主理人的年龄、阅历甚至心情来变化。民宿更像我给自己创造的一个大型玩具盒子,它能经得起我玩5年、10年甚至50年。我其实是迈入了我所期望的有质量的生活。”

我不知道王小花最终是否能够建成她理想中的园子,但她的热情唤醒了我曾经的悸动:做一个民宿老板娘。2013年,我在泰国清迈旅行,在热闹的老城住了一晚后,我搬去了城外的一处“Home Stay”。那栋带着小庭院的老别墅位于游客罕至的安静街区,有宽敞的客厅,舒服的沙发,扎实的木地板,泰式风格的雕花楼梯。年轻独居的女主人一手打理着上下四个房间。每天早晨,我在鸟语中醒来,就看见她在厨房里变着花样做早餐:各色水果、煎薄饼、瘦肉粥、三明治、泰式小吃……每一样端上来都是满满的心意。闲暇时,女主人爱做手工,会邀请有兴趣的客人加入。若是遇到天灯节和水灯节,她会在花园里备好材料教大家做河灯,带着他们到河边放灯祈福。这种偏安一隅的生活,看上去自给自足,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平淡又快乐。
这几年,民宿的火爆是显然易见的。那些奔赴远方回归生活的民宿主人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甚广。从去年开始,湖南、江苏、浙江、东方四大卫视都推出了以民宿为主题的明星经营类综艺节目。我的朋友圈里,一些人已经将心动变成行动,在云南、海南等地与人合伙开民宿。更常见的,过去两年的节假日,朋友们在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游玩,很少会有人晒居住的酒店,但民宿不一样,它和有品位、有格调、爱自由、会生活的人设紧密相连,是诗与远方的天然搭配。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17年民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民宿数量从2016年末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末的20万家,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咨询服务机构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中国在线民宿预订的交易规模突破100亿元,2018年会突破200亿元。浩浩汤汤的潮流之下,民宿的魅力究竟在哪儿?

理想国
2017年,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一份《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这份文件将民宿正式定义为“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同时,这份文件称,它所适用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客栈、庄园、宅院、驿站、山庄等”。
早在“民宿”流行之前,客栈、庄园、山庄已遍布全国旅游胜地。而“民宿”二字在中国的使用肇始于2006年之后的莫干山。
2002年,杭州媒体人夏雨清在莫干山租下了一栋旧宅。这栋旧宅是1930年宜兴富商潘梓彝建造的“颐园”。2000年,夏雨清第一次见到它。无人打理的院里长满一人多高的荒草。前门是锁着的。夏雨清从破旧的窗子翻进去,看到雨水从屋顶滴滴答答地漏下来。房子虽然破陋不堪,但它击中了夏雨清:恰值秋末,满院子绯红的枫树和香甜的金桂都是1930年以前种下的旧物。
2002年租下颐园后,夏雨清花大力气把房子修葺一新,在当地了雇了个阿姨,负责打理房间,烧饭做菜。他告诉我,那些年女儿年幼,一家人住在莫干山的时间比杭州更多。颐园有六个房间,除了一间自住,其余的间或拿来招待朋友,自得其乐。他没想到的是,2006年,在上海做出版业的英国人Mark Kitto想隐居写作,于是在莫干山开了一家叫The Lodge的咖啡馆。他的外国朋友前来做客无处歇脚,颐园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那以后,2007年,法国人司徒夫找到一个叫“仙人坑”的废弃茶厂,买下了茶园所在的120亩地,建了“法国山居”。南非人高天成在劳岭村一个叫山鸠坞的地方租下几栋房子,建成“裸心乡”。司徒夫和高天成都曾是颐园的住客。这些外国人在莫干山的出没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最开始,媒体把他们称作‘洋家乐’,但后来大家逐渐开始使用‘民宿’一词。”夏雨清说。于是,追根溯源,颐园成了莫干山民宿第一家。
文章作者


徐菁菁
发表文章143篇 获得36个推荐 粉丝1762人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记者。写字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