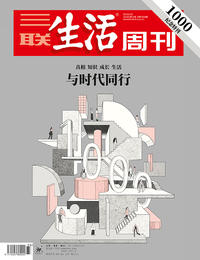姜文态度:追寻“真”的方向
作者:蒲实
2018-08-16·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525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一
看姜文经典之作《鬼子来了》,里面的符号既熟悉又陌生。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被动面对外部世界切入,需要决定向何处迈出脚下一步,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为此争吵和不决。电影充满符号的隐喻。马大三埋人不成,跑进屋与三嫂迎面撞上,就到床上往被子里钻,钻完躺在床上,与鱼儿和小六子对望。鱼儿和小六子的眼睛很亮,像天上的星星,马大三就想带上小六子和“七爷”跑出村去。七爷是谁?是个滑行在铺床轨道上,喊着“我一手掐吧死俩,刨坑埋喽”的残疾老人,也是村民中唯一敢担责任的人,当然是精神上的担责任。对望的三双眼印象深刻。《纽约,我爱你》姜文导演的片段里,最后出现的照片上也有这样一双斜望的眼睛,就像他的个人签名。
姜文导演的六部电影都在处理历史。他说,从后往前看,很多时候是“马后炮”,“已经发生了,倒推觉得可能是那样的原因,跟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是一回事”。昨日之日不可留,往日之事不可追,实际发生的情况究竟是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他在河北蓟县的一个村庄设置了一种原始状态,一个外部世界任何消息都到达不了的封闭村庄。村里的人不受任何历史成见的影响,也不认识日本人,对他们既不怕又不恨。他们生活在生命形成一个小闭环的共同体里,从来没有外来人来过,就像我们的集体意识被设置成与日本人初次发生接触的状态。他们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吗?电影里的符号体系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理解起来已拉开了时间上的距离。比如,花屋小三郎差点被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善意同化,把随身带的神符挂到了马大三养的鸡上。那竟是善良的马大三唯一一次真动怒,大喊着“要我们的命”,把花屋狠揍一顿。这个村庄实际是姜文的老家。他出生在唐山市,出生后不久,他妈妈将他送到乡下姥姥家。他的姥爷那时被发回原籍,姜文就在姥姥家长大,直到10岁。他很了解那儿的人怎么思考,气氛怎么样,“我对我老家有话语权”。
姜文告诉我,他也曾试过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去想问题,但发现“那不太真实”。实际上,“民族主义”过去并没有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里诞生出来和存在过。他说,自己中国生中国长,“只能从中国人内部去思考,比这个更高的视角,毕竟有限”。他说,他学习了解日本人怎么想,为什么这么做,但仍然是中国人的思考,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德国人的作品,写《圣经》的人生长在西奈半岛上,“他们是那里的人,才写出了那样的作品”。“我”的视角在姜文那里根深蒂固,他不假装也不试图让自己成为其他人。

“我”是贯穿姜文电影的主题之一。马大三被一个神秘的“我”,深夜敲门、拿枪顶着脑袋,接下了花屋和翻译董汉臣。“我”不露面,成了一个隐喻符号,参与了很多经典台词。比如,村民对“‘我’是谁”的追问,“我怕这个‘我’”的恐惧,董汉臣将“‘我’是谁”翻译为“他们是谁”的另一重视角。对“我”的找寻,也视觉化在马小军从镜中看到自己,张麻子从半自觉的人物变成自觉的过程,马走日的本色出演,三个爸爸和关巧红都离开后迷惘地站在屋顶不知向何处去的李天然中。对“我”的找寻过程中,历史呈现出它的一种“真相”。电影里这些人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言说的联系:张牧之跟在火车后骑着马去浦东,马走日乘着火车从上面离开,李天然乘着火车从旧金山回到北平;《邪不压正》的海报上,李天然做出“六”的姿势,是《让子弹飞》里“小六子”的符号。
姜文很喜欢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禁闭岛》。它和马大三怕“我”一样,它的“真相”指向自我的潜意识深处,最深的恐惧是对自我的恐惧。姜文说,无论是村庄还是岛的封闭性都没有必要专门去设置,这其实是人的状态本身,“我们都封闭在自己的大脑里”。全球化和更便捷的沟通也无法打破这种封闭,“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都存在于自己的头脑中,我们也天生封闭在自己的躯壳中”。
人和人的误读于是成了常态,理解反而很难。姜文至今仍在不断去理解父亲母亲,这种理解他说要贯穿一生才能完成。姜文电影里,人物之间的语言和行为大多有翻译这个视角。《让子弹飞》里一句经典台词,张牧之让老汤“你他妈给我翻译翻译”,情感非常复杂。这部影片还有一个英文副标题,翻译过来叫“一部西方传奇”。英文海报上,一片风中飘的白色鹅毛托起一枚金色子弹。姜文曾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他的电影有西方戏剧的影子,但这些本身也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思维的一部分。在中国100多年西学东渐和近现代化的历史中,“西方对中国影响很大,马克思主义也是德国的产物。翻译对历史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
翻译的“锚点”在自我。十八九岁姜文在中戏读书,从艺术概论学到,作品一旦离开创作者面临欣赏者,就已产生自己的生命,“欣赏者如何对待它,与创作者没有关系”。欣赏者的理解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在他看来,作者与观者达成一致没有意义,误读才是普遍存在和有意思的。“每个人从电影中看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映照出他自己的一部分。”“真相”也就与“我”这个自己紧密纠缠在一起。误读可能是危险的,但也可能是美好的。爱情就建立在误读上,“俩人非觉得彼此与众不同,就有了爱情”。
文章作者


蒲实
发表文章153篇 获得23个推荐 粉丝1983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