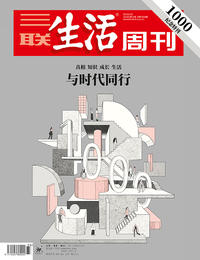偶然回首,文字所教会我的一些
作者:蒲实
2018-08-16·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632个字,产生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一
2013年2月,我在华盛顿出差,住在离智库和使馆云集的杜邦圈不远的一家宾馆。那次是去围观奥巴马连任的就职典礼。到达华盛顿后,我写了两篇年度爱情专刊的稿子,其中一篇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这篇实际上是一篇虚构小说。我把它设置在我比较熟悉的欧洲,用人物口述、我为记录者的形式,从男性角度,实际上以“性别镜像”的方式,想象对方的所见所思,将其写了下来。故事原型的内核,是从朋友那儿听来的别人的故事。
交稿的第二天早晨,主编朱伟发来一条短信:“第一篇太好。要每一篇都这么好就好了。”主编是个一向严厉的人,收到他的短信,我备受鼓励,但竟有点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他的“第一篇”究竟是指哪一篇。我同时交了两篇,自觉这一篇虚构写得生涩羞怯,必定比不上另一篇我所熟悉、且自我感觉写得较为充分的采访写作。这两篇放在同一封邮件里交稿,虽然虚构那篇放在附件第一条,后来杂志出来,也是这一篇排在前面,但“位置”不能说明问题。“第一篇”究竟是哪一篇,在我这里成了一个悬置的小疑惑,被暂搁脑后。
5年后,我正写沈从文。写作家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份有些超出自己写作资历的任务,我更把它视为一个通过阅读、采访和写作来探寻接近作家之路的机会。读沈从文的文字,让我对“爱”有了另一层体悟。沈从文是一位在极端困苦的时代和环境里生活过的作家,目睹了很多屠杀和死亡情景,也经历过生活的贫穷和颠沛流离。他几乎是从地狱之上去看人世间的,书写的目光里却始终充满对生命的爱——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爱了全世界”的。他小说里人物的命运大多因一个“情”字的驱使而富有悲剧性,为情而颠沛流离、生离死别。这也是“新文化运动”还未深刻改变中国文化的前夜,尚未“觉醒”的乡村人朴素的生命动机和命运牵引力。在沈从文那里,我逐渐触碰到让死亡与爱密不可分的那条无形引线,在现代人的情感体验里它遁形已久,此刻被唤醒了。
在那期间一个写稿至深夜疲惫的时刻,我突然理解到主编当年短信所指的“第一篇”,正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那篇文章里,两个互相倾心的人在异乡相遇后分别。不久“我”出了车祸,车在丁字路口拐弯处被皮卡车撞进副驾驶座,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我”突然意识到,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微小错位,那正是因爱而生的思念,便立即买机票去追赶已经离开的女人,但她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我”,只留下多年后回望时的温暖记忆。文章短小,5年前写的时候,我并未明确“死亡”的角色,而将其视为制造戏剧性的元素。5年后我才懂得,这个故事早已确立了“死神”为它自己的主角,而写的人浑然不觉。
故事里写他们短暂共处,“我”总准时开车接她,她总迟到几分钟,“我”总耐心地在车里等待几分钟;这只是寻常温情。这一点心理与机械时间的微小差,与后来“我”与死亡之间的距离相照应,却将爱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人对离别虽有不舍,但她选择顺流而下,按原计划踏上归程,互生的好感本应画上句号。如果她未曾离开,车撞进和吞噬的地方就是她平常坐的位置,死神或许将降临在她头上,又或许将不会有车祸——命运分岔的小径通向何处,取决于偶然。然而,死神降临的瞬间,“我”下意识担心的是她是否安全,又欣慰她已不在,却证明了爱情的真实,将他推向她。5年前,当我写她得知“我”在订机票,惊呼让“我”不要去找她时,仅是出于一种还不够清晰的道德直觉和让故事流畅的语感;多年后回望我才明白,这种拒绝是一种对命运的知晓,在我写的时候,其实还一无所知。无意之间触碰到的道德,是我几年后读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分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才变得清晰起来的,我至今还只是理解了皮毛,远未透彻理解。2014年再度给爱情专刊写稿,那一期的主题是《天上爱情,人间婚姻》。我把自己完全缠绕进去,却也未能向自己破解爱情与婚姻的诸多问题。稿子被主编毙掉后,我反而安心了下来,感到得以暂时解脱。这说明,我对爱情还没有形成深刻完整的认识,远未达到2013年2月那篇文章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深度——文字一旦完成,实则就与作者分离,我只是它的近邻。
直到时光流逝,我才从中理解了这些。理解之后,我哭了一场,既为当年的浑然不觉,也为刹那间通过文字与死神和爱面对面的领悟。也是从这里,我开始领会到,文字里的“时间”不是对现实时间的全然复制和模仿,而有它自己的真实,写作的人不过是顺应这种召唤。写作者通过开启“时间”,实际上也构造了时间穿行其间的“空间”。那么文字应从何处开始?写沈从文让我认识到,生命与爱是推动他文本的源头动力之一。
文章作者


蒲实
发表文章153篇 获得26个推荐 粉丝1983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