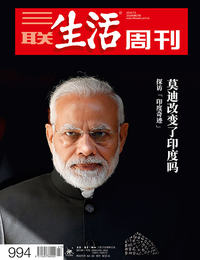寻找“印度模式”:未来之国的当下真相
作者:刘怡
2018-07-04·阅读时长3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7180个字,产生18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贫民窟里的中产阶级
列车摇摆着穿过“岛城”(孟买南部半岛地区的俗称)的心脏地带,不紧不慢地驶向南方。距离由阿拉伯海方向吹来的西南季风(Monsoon)抵达南亚次大陆还有半个多月,孟买市在每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8摄氏度。像本地的许多客运列车一样,这趟由印度西部铁路局(WR)运营的海港线慢车没有空调设备和窗玻璃,顶棚上垂头丧气挂着的风扇叶片纹丝不动,车厢门自始至终敞开着。灼热的阳光很快令金属座椅和把手的触感变得温热,我开始尝试像本地人一样“挂”在车门后方的扶手杆上,以便接触到列车前进带起的凉风。
我们正在驶入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前一天下午,我已经在极近距离上观察过它的样貌。因为日晒雨淋而污损发黑的砖墙像高峰时段的地铁乘客一样拥挤在一起,顶部用简陋的石棉瓦或防水油布覆盖。提着空水桶出门的少年、随意晾晒在屋檐下和道路两旁的衣物与无人清理的街头便溺物一样俯拾皆是。从社区中心那些相对较高的住宅楼(大部分间距不足2米)之间穿过时,你可能会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惊到——那些雇员达到上百人的纺织品和成衣加工厂,就设在大型住宅楼的半地下层,透过气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们黝黑脸颊上的汗水。当然,永远不会缺少在印度任何地方都异常活跃的牛犊;它们通常会被随意拴在某幢楼的拐角处或者小胡同的出入口,百无聊赖地用尾巴驱赶着虻蝇:牛和它的主人一样瘦骨嶙峋。

从纵贯市区的铁路上打量达拉维,一定程度上隔绝了这些真实的感官不悦。车站的外墙遮挡住了从贫民窟所在的高地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的墨绿色污水(它们依然可以从另一侧的公路上被观察到);在午后的烈日下,很少会有居民在室外游荡,从而给观察者造成了一种人烟稀少的错觉。但统计数字是真实而残忍的:截止到2016年底,在达拉维这块2.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仅相当于北京植物园面积的一半)上常住有60万~100万人口,平均1450人共用一个厕所,社区医生和志愿者每天要处理将近4000例伤寒病患。印度政府在2010年曾计划彻底拆除和重建达拉维,但因为困难过大而搁置:即使是最简单的原地翻建,预估成本也超过了20亿美元。而像这样规模的贫民窟,在孟买市和都会区另外还有4处,居民数量接近当地总人口的1/4。
从新城中心的四星级酒店南下达拉维,我们拜访的对象是52岁的外贸商人巴特拉。这位加尔各答大学MBA名下开设有一家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一家摩托车配件厂和一家工业涂料商贸行,而他的大部分订货商和下游企业就分布在达拉维周边。“贫民窟里有我的许多社会关系、商业伙伴网络和危险化学品仓库,我们印度人并不会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巴特拉在他安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向我介绍,“在我的父亲成为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之前,他也居住在达拉维。”按照这位年销售额超过50万美元的小富翁的看法,达拉维是一块不折不扣的风水宝地——这里有全孟买租金最低的厂房和办公室,进出口货物可以便利地从10公里外的港区运进运出。从外省前来投靠亲友的年轻人通常都会在达拉维找到第一块便宜的栖身地,并顺利觅得第一份可资糊口的工作。“政府希望杜绝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弊端,要求我们尽快将仓库和厂房搬到北面60公里外的瓦赛东(Vasai East)工业区。我才没那么傻哩!那个‘工业区’每天停电至少3小时,谁来承担损失?”
巴特拉理直气壮的发问,很难说是褊狭之见。严格说来,达拉维不仅不应当被称为低收入社区,甚至可以说是孟买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日起,低廉的租金和从全国农村涌入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吸引了大量纺织工厂、制衣厂、皮革和首饰加工厂以及制陶作坊入驻当地,5000家中小企业和15000个生产车间的年营业额在21世纪初已经上升到了10亿美元以上。整个印度西南海岸的废品回收业都以达拉维为中心,创造出25万个工作岗位。专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信贷网络以及法律顾问公司的广告也随处可见。不同机构的经济学家计算出达拉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预估的2017年全印度人均收入(近1500美元)接近,显著高于比哈尔、拉贾斯坦等北部农业邦。除去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生活服务设施外,达拉维居民的识字率高达69%,是全世界城市贫民窟中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地的恶性治安案件发生率并不显著高于印度其他地区——尽管按照全球中等收入以上国家的城市治理水平,肮脏炎热、空气和水源污染极度严重、四处飞溅着电焊火花的达拉维实在可算是人间地狱。
“美国人扭曲了我们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长期关注印度问题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会政策编辑艾玛·邓肯(Emma Duncan)在邮件中告诉我,“‘中产’一定等于带花园的小洋楼、私家车、英式下午茶茶具和每年好几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吗?显然不是。但当我们提起‘未来印度的3亿中产阶级’时,用的恰恰是这种被高估的标准。”所幸巴特拉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样本,一个达拉维家庭在时代变迁中实现阶层上升的活生生案例——“像许多印度中小企业的创办人一样,30年前,我用父亲和叔叔的借款开办起一家小商行。”巴特拉回忆道,“从国有大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永远微乎其微,但我依然感谢拉奥总理的自由化改革,使我可以直接承接来自欧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订单。如今我在8个国家有固定的客户,住上了新城区的独栋小屋,和我年纪相仿的不少伙伴经济状况也有了改善。而这都应当归功于达拉维:没有它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便宜地租和社会关系,恐怕我在1998年核危机之后的那个低谷期就已经倾家荡产了。”

巴特拉口中的达拉维式“社会关系”,折射出的是传统人情在市场经济模式下被赋予的新价值。当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农民从中北部地区涌入德里和孟买,种姓制度对他们构成的桎梏已经微乎其微,但家族关系、同乡情谊和基于关联产业形成的合作关系始终存在。通过这张富于本土化、平民化特性的关系网,父亲和兄弟为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中介公司组建以邦为单位的招工网络,财务公司以相对公允的利率拆借资金、帮助小公司渡过难关。1998年印度政府违背《核不扩散条约》、自行宣布成为核武国家之后,来自欧美的外贸订单急剧减少;在将近5年时间里,是底层社会关系中那种朴素的风险共担意识让达拉维的诸多中小企业主可以咬住牙关,通过债务延期、迟发薪酬等手段将公司继续维持下去。“达拉维人有自己的道德观和商业逻辑,”巴特拉总结道,“即使没有政府,我们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这才是印度社会真正的基石。”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30个推荐 粉丝2498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