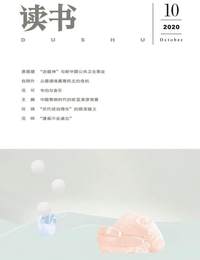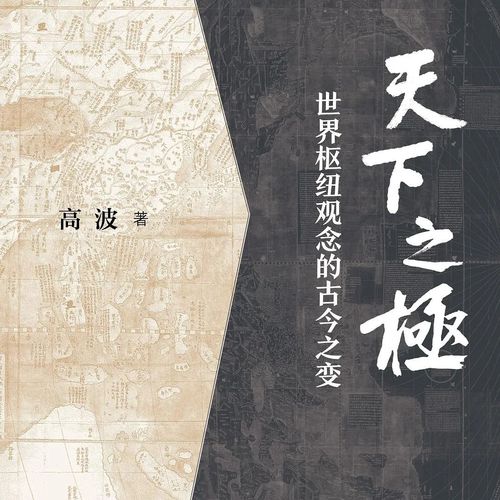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吃瓜时代”文学与政治的交互关系
作者:读书
2020-10-21·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754个字,产生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骆贤凤、郝一帆
刘震云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其此前出版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一脉相承,继续将写作的焦点聚焦于社会底层,延续了借普通人物揭开官场中权、钱、色的交易黑幕这一写作模式。但是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着重刻画了一个同社会热点紧密相关的主角 ——“吃瓜群众 ”。纵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他的作品紧扣社会现象,用幽默、戏谑的笔端将个人的政治思考融入文学作品之中,通过文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吃瓜儿女”的象征性
“吃瓜 ”一词源于网络语言,与其相关的网络语还有 “吃瓜群众 ”“不明真相 ”等,意为对事件本身真实性并无兴趣、仅仅以该热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静坐吃瓜 ”的看客。“看客 ”形象在鲁迅的文中早有塑造,鲁迅在其《野草·复仇》篇中是这样刻画 “看客 ”的:“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在鲁迅的笔下,“看客 ”们从远处聚集于一地,他们身份各异、有老有少,但这不影响他们一同津津有味地“看煞 ”争斗者,他们渴求鲜血。“看客 ”猎奇、好事的心理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民族心理的体现,它作为一种不可泯灭的民族基因延续至今,直至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群众 ”的出场。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其《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书中提出:“除了我们的即刻意识 —它是完全个人性的,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经验性精神(尽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而接受),还存在着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是单独发展而来的,而是遗传而得的。”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儿女 ”正是同鲁迅笔下的 “看客 ”一脉相承。“吃瓜儿女 ”们身上同样镌刻着猎奇心理,但科技发展,看客们不必再由四面八方上街聚集,大可在空调房里啃着西瓜、顺着网线对公众人物进行 “公开处刑 ”。此外,“吃瓜群众 ”比起 “看客 ”更多了一分话语参与度,鲁迅笔下的看客更多的享受来自鲜血对感官的刺激和共鸣,但是 “吃瓜儿女 ”们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话语 “制裁”不公之事与人。如小说中的公安局局长杨开拓只是由于紧张,所以在事故现场无意识地被吓得傻笑,但是他的笑被群众拍了下来放到网上之后就变了意味,“傻笑 ”变成了意味深长的、隔岸观火的 “开心的笑 ”,由此更有网友借辱骂杨开拓,延及社会和政府。
但是 “吃瓜儿女 ”了解的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与其说他们是在伸张正义,不若称之为一种情绪宣泄,见到貌似社会不公之事,吃瓜群众便怒发冲冠,开腔国骂。这种情节设定无疑是刘震云有意为之的对 “吃瓜群众 ”的戏谑,无关真相,娱乐至死。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