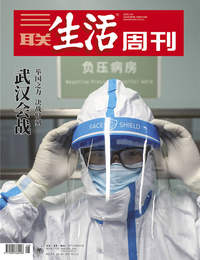奉俊昊:奥斯卡的闯入者
作者:宋诗婷
2020-02-21·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327个字,产生1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奉俊昊和《寄生虫》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重新翻看过往的采访文件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些当时笃定的说法后来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戳穿,白纸黑字间全是嘲讽。有些对话是今天的佐证,像是一份计划书和预言。也有些内容是不清不楚的,采访对象自己也不确定,再联系后来发生的事,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2014年,《雪国列车》之后,我曾采访过今天的奥斯卡导演奉俊昊。回看当时的采访,内容涵盖计划书和“不清不楚”,那些对话或多或少地都指向了《寄生虫》的创作和那之后奉俊昊的奥斯卡之路。
当时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弱者之下,还有弱者》,如今看来,那几乎就是《寄生虫》的核心主题。我们是在说起《母亲》那部电影时,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总是对‘虚弱的人’感兴趣,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人真正的本性是什么?我仍在学习,给不出确切的定义。通过角色,我在赋予同情的同时,也表达对人性的怀疑和恐惧。不要陷在电影的表面逻辑里,因为弱者之下,还有弱者。”
他还提到了“让电影保持开放的结局”。“只有在好莱坞电影中,事情才能方便地得出结论。而我认为,这在现实世界中不会发生。在技术上,开放式结局也可以让影片对观众产生更持久的情感影响。”
当时,在很多问题上,奉俊昊都会提起好莱坞,那大概是《雪国列车》的后遗症。那个时间点,奉俊昊正在反思那次票房和口碑成功,但自己表达颇受局限的合作。“我确实对接近好莱坞及其市场和资本持谨慎态度,我见过许多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天才导演在好莱坞毁掉了一切。所以,我很警惕,在很小心地走,我必须要我的创造力受到保护,才可以把控自己的电影。”
六年前那些早已明确了的创作主题,那些与好莱坞的关系探索如今都在《寄生虫》中找到了呼应。和把社会、阶级装进一列火车的《雪国列车》相比,《寄生虫》用具体空间隐喻无形社会的呈现更直接,手法也更精巧。在这部介于现实主义和寓言之间的作品里,一户穷人千方百计混进富人家工作,为了自保,他们不得不排挤、陷害更走投无路的人,甚至痛下杀手。
这是一个典型的“弱者之下,还有弱者”的故事,里面几乎装进了奉俊昊一路走来攒下的所有电影技巧和元素。希区柯克式的悬疑、小人物的黑色幽默、财团垄断、朝韩问题……《寄生虫》不像奉俊昊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它是它们的总和。
显然,《寄生虫》也让奉俊昊摸清了自己与好莱坞的关系。这是一部在韩国本土创作完成的电影,主要投资也来自韩国。他没让自己适应规则,成为好莱坞的一员,他以“闯入者”的身份成为奥斯卡92年历史上最令人意外的大赢家。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29个推荐 粉丝83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