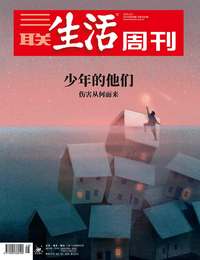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
作者:刘怡
2019-11-27·阅读时长1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286个字,产生1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10月17日,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首府拉姆安拉附近,以色列警察与巴勒斯坦示威者发生冲突。拉姆安拉属于《奥斯陆协定》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A类地区,但其周边依然常年驻扎着以色列军警(视觉中国供图)
“什么是巴勒斯坦?”
班克西(Banksy)在伯利恒隔离墙南面投资兴建的这家旅馆,相当戏谑地化用了老字号豪华酒店品牌华尔道夫(Waldorf)的谐音,唤作“以墙围之”(Walled Off)。前台提供的入住手册不无骄傲地宣称,这“可能是全世界视野最差的一家旅馆”——所有10间客房的阳台都正对着3.6米外包围拉结墓(Rachel's Tomb)景点的混凝土隔离墙;在眺望到耶路撒冷的夜景之前,你的视线必须首先划过4~8米高的围墙、镶嵌其上的带电铁丝网以及外形犹如潜望镜一般的以色列国防军瞭望塔,并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填满整个墙面的彩色涂鸦。前厅一角的一间暗室里端坐着一具与真人等大的英国绅士蜡像。主人公西装革履,右手紧握钢笔。访客们按动电钮,钢笔便会自动在面前的白纸上留下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签名: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和这位从未公开身份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一样,贝尔福勋爵来自英国。1917年11月2日,他以战时内阁外交大臣的身份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代表英国政府承诺“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蜡像手中的钢笔还原的,便是贝尔福在那封信函上的签名。一般认为,这份《贝尔福宣言》揭开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序幕,并为随后以色列国的出现乃至中东地区一系列暴力冲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班克西的围墙旅馆,正是为纪念《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而兴建。在此之前,这位年轻艺术家在西岸创作的一系列以反战为主题的街头涂鸦形象,例如掷花示威者、穿防弹衣的和平鸽以及对以色列大兵搜身的小女孩,在欧美世界已经收获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旅馆的选址最终被确定在1996年建成的拉结墓隔离墙附近;长墙面向伯利恒市区的一侧,如今成为全球来访者挥洒涂鸦兴致的俱乐部。“你们把暴政的象征物弄得太像一件艺术品了。”我的阿拉伯司机艾哈迈德不禁抱怨。

班克西在伯利恒隔离墙近侧修建的围墙酒店(左),靠近酒店的墙体已经成为全世界街头涂鸦爱好者的反战作品展示地(视觉中国供图)
作为围墙酒店的一名住客,理论上我已经身处巴勒斯坦国约旦河西岸省份伯利恒(Bethlehem)的首府,并且属于1993年《奥斯陆协定》规定的完全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管辖的“A类地区”。飘扬在隔离墙近侧的泛阿拉伯四色旗以及街头身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都在明示:此地便是联合国大会第43/177号决议(1988年)确认为合法的那个“巴勒斯坦国”,是阿拉法特和爱德华·萨义德的故乡。然而这种以历史文献为凭据的结论,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另一些更直观的视觉符号的挑衅——当我从伯利恒乘坐出租汽车返回耶路撒冷时,会发现就在围墙酒店北方1.2公里处,混凝土防爆墙上开出了一个四车道的口子,顶端悬挂着一块醒目的彩钢标志牌,上面写着:“以色列旅游部欢迎你”。而从耶路撒冷进入伯利恒的旅客却看不到任何宣示国别特性的符号。同样,持以色列签证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外国游客不会受到任何边境管理人员或者海关官员的盘问。你可以游遍整个西岸地区,却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已经身处以色列国境之外,仿佛巴勒斯坦国并不存在。
从约旦西部跨越艾伦比桥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在大桥东边,侯赛因口岸的约旦官员给你的护照盖上出境章,远远看着你登上过境大巴车。但当汽车行驶到大桥中央时,你的视线中突然出现了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根据1994年约以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经太巴列湖(加利利海)注入死海的约旦河航道中线构成了两国的北段国境线。尽管这条边界超过3/4的部分和巴勒斯坦国的东段国境线重合,但双方都认为“这一状况并不影响约以之间的划界”。于是,在从未获得巴勒斯坦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接管了毗邻约旦的整条边境线以及所有出入口岸。在艾伦比桥西面迎接你的是礼貌但充满警惕的以色列安全官,警用装甲车顶部的活动机枪塔在路障背后探头探脑:只有拿到以色列入境卡,你才能踏上西岸的土地。
假使你选择取道1号高速公路,由边境口岸直趋被以巴两国同样奉为首都的耶路撒冷,感受只怕会更加微妙。这是一条专供以色列车辆使用的六车道全封闭公路,全长94公里,铁丝护栏以及间或闪现的集装箱检查站(用多个集装箱箱体改造而成)明白地宣示了它的所有权归属。尽管公路的边境区段靠近巴勒斯坦城市杰利科(Jericho),但围栏和隔离墙小心地确保了彼此疑惧的人们永远不会发生接触;沿途视线所及的只有凯法尔阿杜明(Kfar Adumim)和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地区被隔离墙团团包围住的犹太人定居点。只有在穿越山区的路段,你才能观察到本地巴勒斯坦人使用的乡间公路——它们与1号公路基本平行,但地基矮了整整一截,宽度通常不超过四车道,时不时会有牛群穿过。一个巴勒斯坦人只有仰起脖颈、让视线越过铁丝网和路基,才能观察到从头顶上方呼啸而过的以色列车辆,一如他们仰望一墙之隔的犹太人定居点。

周五清晨,前往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主麻日礼拜的西岸妇女排队通过卡兰迪亚检查站(IC photo供图)
距离《贝尔福宣言》公布已经过去了102年,“什么是巴勒斯坦?”(What is Palestine?)依旧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公元1世纪到1948年,巴勒斯坦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享这片地中海东岸的贫瘠土地,也一同充当从罗马人到英帝国的一系列外来征服者的子民。1948年之后的40多年里,巴勒斯坦是一个“待建立”的国家:联合国大会的分治决议赋予了本地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但供其建国的领土要么处在邻国埃及和约旦的控制之下,要么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人们把1948年和1967年战争期间逃往异国他乡的500多万本地人及其后代称为“巴勒斯坦难民”——严格说来他们仅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以色列作为确凿无疑的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的非犹太人只能把巴勒斯坦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民族标签。而在1993~1995年的两份《奥斯陆协定》生效之后,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临时”国家。在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以色列的外交承认的同时,它也被迫将一切“现状”(Status quo)——隔离墙和被剥夺的边境线、犹太人定居点和以色列车辆专属公路、不定期出现的以色列安全部队——一并收下。有时你不禁要惊叹人类在政治活动中的想象力:一切违背常识的现象,最终都被心照不宣地默认了。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2502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