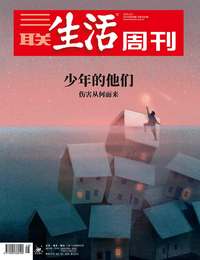姚建龙:什么是罪错少年需要的正义?
作者:刘畅
2019-11-27·阅读时长2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0895个字,产生9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姚建龙(金海 摄)
大连13岁少年杀人,因未满14岁,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引得舆论一片哗然。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姚建龙看到的,却是不同社会对少年观念的差异。作为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他向我们讲述,面对屡屡发生的少年极端恶性事件,司法应如何坚持自身的正义。
少年法的意图
三联生活周刊:大连13岁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后,作案人因年龄未满14岁,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目前的处理办法是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认为法律没有实现正义。从专业角度看,对于类似的少年犯罪的极端事件,司法界关注的是否同样是刑罚的问题?
姚建龙:类似的极端案件在各国都有,日本有两个案例最为典型,可以作为对人们面对类似案件的反思。
其中一个案例是“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也是未成年人杀害未成年人,但性质比大连杀人案要恶劣得多。1997年,一名日本神户市的14岁学生在3月至5月间,分别杀害了一名11岁男童和一名10岁女童,其中杀害男童的行为尤其残忍。
少年的暴行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全民的恐慌,当时日本的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是16岁,也就是说,这个少年不可能受到刑罚处罚。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对该少年的处理方式。不能适用刑罚是否就“一放了之”呢?
少年被逮捕后,依据日本的《少年法》,他的信息被完全保护起来,只以“少年A”作为称呼。少年法院发现少年A的家庭存在问题,少年A的母亲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强迫他在学校表现突出。即使社工提醒这位母亲,少年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在当时已经把虐待和杀害小动物当作“嗜好”。最终神户家庭裁判所判定将他送入有医疗性质的“关东少年感化所”诊疗,之后又将他送到次一等的“东北中等少年院”。2004年已经成年的他获得全新的名字和身份,重新进入社会,没有再犯罪。他之后还主动出书,记录自己曾经的经历。
这个案件说明,即便面对恶性少年,少年司法的首要原则不是报应,不是“一罚了之”,而是“以教代刑”,也就是“宽容但不纵容”。有人可能会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表达极大的不满,罪行如此恶劣竟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更没有“杀之而后快”!的确如此,在当时的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这个案件,2000年时日本修改《少年法》将可以适用刑事处分的年龄调低到了14岁,这也被中国的一些学者解读为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这一法律的修改一直饱受争议,事实上迄今也没有真正适用过。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少年A被判处重刑而不是留在少年司法体系中教育矫治,他是否仍然可以顺利回归社会?
日本的《少年法》于1922年颁布,在1948年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是一部完全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少年司法拥有特殊理念、特殊立法、特殊机构、特殊程序、特殊处理措施。简而言之,它着力淡化“罪”的概念,在中国被视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违法事件,在日本被称为“非行”,它的目的不是报应,而是保护。与家庭法院配套的是系统的保护处分措施,以及各级少年院。少年院不是监狱,更像一个学校和医院。少年犯再大的罪,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保护处分”而不是“刑罚”。
另一个案件是更为知名的“福田孝行杀人案”,这个案例能够说明当作案人的性质过于恶劣时,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惩罚、报应的目的。
1999年4月14日日本山口县光市,18岁的少年福田孝行闯入民宅,企图强奸23岁女屋主未果后,先将女屋主杀害奸尸,又将爬过来的婴儿活活摔死。日本的成年标准是20岁,而福田孝行最终被判死刑,似乎成为一个重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8岁以下不得判处死刑,这是全世界认可的底线,福田孝行当时已经年满18岁,并没有触碰这条底线。
他能够判处死刑,最首要的一点是因为行为过于恶劣,负责审理14岁至20岁少年非行事件的日本家事法院放弃了管辖权,把这个少年剔除出了少年司法体系,由检察官“逆送”交给了普通刑事法院当作成年人案件来审理,由此才可以适用普通刑法,适用刑罚处罚。这在法理上也被称为“恶意补足年龄”,即未成年人做出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主观恶性程度极高,则可以剥夺“未成年人”身份,当作成年人由普通刑事司法体系而非少年司法体系来处理。
文章作者


刘畅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8个推荐 粉丝502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