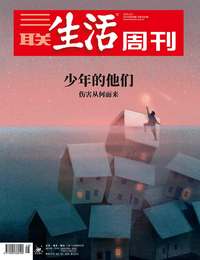校园欺凌:被忽视的“精神绝症”
作者:王梓辉
2019-11-27·阅读时长1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871个字,产生19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插图 老牛)
“梦到自己没穿衣服,站在讲台上”
35岁了,黎曾玲终于开始尝试面对那段残酷的青春。让她迈出第一步的是她现在的工作,因为是天津市青少年事务社工管理服务中心的项目部负责人,黎曾玲过往三年都在从事青少年相关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如针对青少年开展的禁毒防艾、法制教育等宣讲活动。今年年初,他们开始了一项新的服务内容——针对预防校园欺凌的小组活动。
在天津市南郊的一所小学,坐在课堂的后面,留着一头干练短发的黎曾玲微笑着,课堂的气氛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很欢乐。这些孩子都已经上五年级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教导的对象”,他们相互之间会嬉戏打闹,为了小礼物特别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用稚气的声音说出校园欺凌的几种类型和它的危害。黎曾玲看着这10位因为有“暴力倾向”而被召集来参与这项活动的孩子们,既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是在看曾经的自己。
但20年前,没有人告诉黎曾玲什么是校园欺凌,也没人告诉她在遭受校园欺凌时该怎么办。“我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最傻的就是,我根本不需要去承受这些的,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我想转个学就好了,但是我没有。”而“没有”的结果是,从高中、大学到结婚之后,她经常会梦到校园里的场景,那个场景要比一众故作残酷状的校园青春电影更加残酷:一个少女没穿衣服,站在讲台上,而下面就是她冷漠的同学。
不需心理学家的专业分析,梦中呈现的意象清晰可辨,这种长期的噩梦显然来自于成长阶段被隔绝于同伴群体中的经历。从初二开始,黎曾玲经历了长达一年以上的被集体孤立,她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原来那就叫“校园欺凌”。刚开始只是一个之前和她关系还不错女生因为一些矛盾不理她,“就像小孩子闹绝交一样的不跟我说话”,然后好像就在一夜之间,班级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孤立她。再到后来变得不只不理她,“比如说站队的时候,我在这站着,他们每个人都会孤立我,就在我那个位置前后空出一米来,就像你有毒气一样”。在青春期,刚刚开始发展出强烈自我意识的少年们甚至不在乎将这种集体孤立的行为大张旗鼓地展示出去。即使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点黎曾玲去黑板上做板书回答问题,其他人也会发出那种很鄙夷的声音,弄得老师也不知所措。
这种欺凌不是在肉体上施以暴力,但伤害程度更甚于肉体暴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从1990年开始研究青少年成长的问题,他曾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小学里给学生们做过校园欺凌的体验,那时他找了一个孩子站在讲台上,用黑布蒙住孩子的眼睛,然后找几个欺凌者对孩子进行一些推搡之类的行为,下面传来了同学们的笑声,宗春山把孩子眼睛上的黑布打开,问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孩子说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攻击,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宗春山问哪个对他伤害大,孩子说是笑声。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社会心理学家劳拉·博加特(Laura Bogart)和她的同事们跟踪研究了4297名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研究结果表明,在那些嘲讽和戏弄停止之后,欺凌行为的情感疤痕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且“欺凌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滚雪球的效应”。过了20年,黎曾玲告诉我说,那些被孤立、被鄙夷、被嘲笑的场景与声音已被她锁入了记忆深处,从未被遗忘。虽多年“不敢触碰”,但那段经历给她带来的改变几乎是根本性的,从那之后,她很少参加班集体的活动,变得独来独往,在高中和大学阶段都没有了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同学,连同学会都不去参加。她自己总结说,原因不在别人,就在她自己,因为她变得不会再那么信任友情。
文章作者


王梓辉
发表文章131篇 获得28个推荐 粉丝355人
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