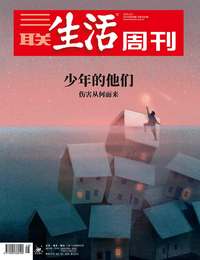困顿少年与他们的成长
作者:王海燕
2019-11-27·阅读时长1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970个字,产生407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如果在成人世界里被忽视,进入青春期后,周围朋辈群体会成为塑造一个人最主要的力量(视觉中国供图)
不被认识的不良少年
刘莎现在还记得2015年的那起案件,通知家长时,和大多数的家长一样,他们很茫然,觉得检察院一定搞错了,直到看到视频,其中一个妈妈当场痛哭,她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原来是这样的。视频是孩子们自己录下来的,两辆轿车里,一辆6个人,一辆4个人,各对着一名受害人扇嘴巴,强迫对方叫爸爸,还拉到一个地方拳打脚踢一番,才兴尽而归。受害者在朋友圈里见过其中一个打人者,知道那是门头沟的“小大哥”钱进。两人随后报了警。
案件是以寻衅滋事移送到刘莎手里的,刘莎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以下简称“海淀未检”)的检察官。这起案件的起因是,钱进被拉到了一个海淀孩子的微信群,在群里跟人吵了一架。钱进找认识的女孩,把群里辱骂他的两人叫了出来,虽然其中一个反复声称,自己并没有骂钱进,但同样被狠狠“教训”了一通。那个让妈妈痛哭的孩子算是钱进的小弟,他妈妈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眼里挺乖的儿子,也会参与到这样的事情当中。
最终,打人的孩子中,两个以“寻衅滋事”被批准逮捕,包括钱进。他那时刚满16岁,经常开着家里的奥迪车,把人带到车里,扇嘴巴,让叫爸爸,有时候也在麦当劳这样的公共场合打人,通常都会录下视频,还威胁对方,如果报警,就把视频传到网上。在他们看来,视频不是法律证据,而是羞辱把柄。

俄罗斯Iksha的少年犯劳改营,未成年服刑人员在进行劳动改造(视觉中国供图)
那次案件,考虑到多方面因素,两个被批捕的少年,以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常规的司法程序,事情结束,附条件不起诉的少年接受考察,决定最终是否起诉。其余人轻松回家。但海淀未检多做了一步,一是在批捕阶段把打人者和家长都叫到了检察院,召开了一次训诫会,家长就是在训诫会上看到视频的;二是督促家长、孩子和司法社工签订了协议,让家长和孩子定期接受司法社工的帮扶教育(以下简称“帮教”)和观察。正是通过司法社工,刘莎才了解到,两个被批捕的少年中,钱进家条件不错,父亲再婚,跟妻子又生了一个小孩,感觉对钱进亏欠,从小宠溺,渐渐养成了各种不良习气;另一个家庭条件困难一些,单亲,爸爸是环卫工,顾不上他,他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刚进入青春期就天天在社会上晃荡。
这种随意滋事,刘莎见得很多,有的是在网上互相看不惯,骂着骂着就找人约出来打一顿,有的是在路上走着,碰到了,吵着吵着也能打起来。以前检察官只关心案件本身,这些孩子从何处来,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可追溯的吗?是环境还是基因塑造了他们,他们是可改变的吗?这样的问题没人关心。
早些年的未成年人案件其实更多,杨新娥是海淀未检的主任检察官,2000年进入海淀检察院,2006年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她记得,当时海淀区未成年人参与的刑事犯罪比例超过了10%,工作压力特别大。当时杨新娥只会办成年人案件,但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司法精神,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应该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预防犯罪为指导精神。杨新娥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办未成年人案子,比如同样的行为,当时外地籍孩子批捕率远高于京籍孩子,因为不批捕的话,公安部门逮捕的孩子就得放掉,外地孩子流动性高,批捕部门有顾虑,怕不批捕孩子就跑了,影响后续进程,干脆统一批捕,关进看守所。对这些孩子,杨新娥很多都做了不起诉处理,因为在他们的年龄,很多行为达不到起诉条件,比如打架、小偷小摸,但这又很容易让人产生暗箱操作的联想。
在一次跨领域的会议上,杨新娥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她想寻找一个办法,科学地理解和评估这些孩子的行为,证明自己不起诉是正当的。首都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首师大”)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以下简称“社工系”)教授席小华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科学评估青少年犯罪问题”正是她的专业方向之一,她正苦苦寻找实践平台。两人一拍即合,让社工加入了海淀未检的工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的两位检察官杨新娥与刘莎(于楚众 摄)
2009年12月,海淀未检首次与社工合作,试点了三个案例,其中一个杨新娥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海淀的大学生案件也归未检部门处理,那个案件的当事人叫胡波,是一名外地来京实习的“大四”学生,偷了同学一部手机,随后案发,在看守所羁押了一段时间。因为认罪态度不错,也得到了被害人谅解,胡波得到了不起诉处理。
但社工王洁发现,虽然没有严重后果,胡波却出现了应激反应,每天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不敢见人,不敢脱下帽子抬头跟人说话,觉得一辈子无法洗刷污点了。后来王洁通过胡波自己和他的朋友、家人、同事、同学,对他做了详尽的社会调查,发现胡波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人品也挺好。王洁发现,胡波偷东西的原因是,当时他“大四”毕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出现了特殊的应激反应,被捕后的异常表现也是他应激反应的一部分。王洁后来把自己的发现和判断告诉了杨新娥,并且告诉她,通过疏导,胡波已经逐渐摆脱了阴影,并且找到了新的实习工作。

玛丽14岁时在学校曾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霸凌,这一经历使得她成年后也缺乏自信(视觉中国供图)
胡波的案件并不典型,但杨新娥还是特别震撼。在她过去的观念里,触犯过法律的人属于边缘人群,他们会回到边缘轨道,青少年同样如此,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如果用不良少年来概括这些曾做出过恶意行为的少年,那曾经的杨新娥只看见了“不良”和不良的后果,很少看到“少年”。
这也让我想起,今年上半年,我曾在西南某地级市采访,和当地一名做专门教育的老师聊起青少年犯罪,他告诉我,自己曾经做基层民警时,经常碰到抢劫偷盗的流浪少年,绝大多数在14~16周岁,只对8类重罪负刑事责任,甚至未满14周岁,不负任何刑事责任,所以必须24小时内无条件释放。做警察时,他只是恨得牙痒,有时候甚至忍不住暴打一顿。他同样不知道这些孩子来自哪里,为什么要抢劫盗窃,他们的未来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群长期处于漂浮状态,并不被认识的少年。
而作为社工专业学者,这些一直都是席小华想要了解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系统研究,席小华曾跟一些未管所、专门学校有合作,但都是项目制,无法长期追踪这些有过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更无法深入了解他们、提供帮助。2009年与海淀未检合作后,2012年,依托首师大,席小华正式创办了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中心(以下简称“超越”),并将合作从检察机关扩展到学校、公安、法院、团委,开始做不良少年社会调查报告,帮助司法机关重新理解这些不良少年。
文章作者


王海燕
发表文章-5篇 获得19个推荐 粉丝718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