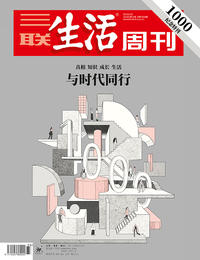敦煌千年之后
作者:张星云
2018-08-16·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968个字,产生2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每个人的历史
似乎每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背后都有一段舍弃城市生活来到敦煌的“艰苦史”。
常书鸿1936年从巴黎毅然回国,冒着抗战烽烟来到敦煌创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待40年;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段文杰用一生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向达两去敦煌,对敦煌文书的研究间接成就敦煌学,也是他真正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提出保护敦煌;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直接去了敦煌,待了50年。
这就像是一种传统。在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四大文明、六大宗教的交汇之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遗存,似乎唯有经历一段舍弃、牺牲与奉献,才能真正在这里做出贡献。
果然,闲谈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也对我侃侃谈起了自己版本的历史。

1984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响应时任院长段文杰的号召成为来到敦煌工作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他们住在莫高窟9层楼前的平房里,土墙、土地和老鼠洞。他一直没法适应喝大泉河的碱水,一开始只是拉肚子,后来牙和肠胃都出现了问题。90年代开始有水罐车从敦煌市里将水拉到莫高窟,2000年后才在机场附近打了井,通过管道将水送到莫高窟。
“生活艰苦倒还好,但如果信息与文化闭塞,是很难搞研究的。”这座曾经丝绸之路的重镇,却在1000多年后极为滞后。当时研究院的通信极为不方便,人们看到的报纸都是一个星期前的,电话也是手摇式电话,需要先接通敦煌市邮电局,再通过邮电局转接,打一个长途电话,往往要等几个小时。如果与全国都存在几个小时甚至一个星期的“时差”,就别提与国际交流了。“真正的改变来自电脑和互联网,它们的出现,才让我们一下子感觉与外界没有差距了。”赵声良说。也正是电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

自1985年起,敦煌研究院先后与东京艺术大学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展开合作,视为敦煌开放之始。当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所有人面前:敦煌壁画最终会消失。如何让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能看到莫高窟,成了最首要的事情。1988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第一期合作项目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让24个人在一座洞窟里滞留40分钟,经过检测,洞窟温度升高了5摄氏度,二氧化碳指数也急剧增加,这些变化都会对壁画造成潜在破坏。
时任副院长的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但她很快发现,不让游客进洞不是个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后来她曾回忆:“人家跟我表演电脑,摁一下一张。我说,你这玩意儿关掉不就没有了?人家说,不会的,它可以永远保存。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于是樊锦诗提出了著名的敦煌数字化计划,在美国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以及浙江大学、中科院合作,以数码照片的方式把敦煌石窟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从此至今的近30年里,敦煌数字化依然是敦煌研究院最主要的工作。
赵声良告诉我,其实除了众人瞩目的敦煌数字化和数字展示中心两大项目之外,樊锦诗另有一个贡献更重要。
1998年樊锦诗刚刚上任院长时,正好赶上一股全国风潮,从秦始皇帝陵开始,各地方政府推广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商“捆绑上市”以增加经济收入,敦煌地方政府和甘肃省政府当时也都积极响应这一办法。为了避免上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樊锦诗开始在各个场合呼吁,在报纸上写文章,可效果甚微,眼前的经济开放是大势所趋。
文章作者


张星云
发表文章193篇 获得12个推荐 粉丝1031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