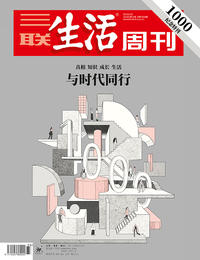探寻桃花源:一个暂时隐匿的世界
作者:贾冬婷
2018-08-16·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701个字,产生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纸上园林
酷暑的天气,又将我拉回到去年夏天在苏州各个园林里穿梭的那段日子。一年的时间像个滤镜,滤掉了40摄氏度高温下的种种不适,滤掉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的干扰,让记忆中的园林复归“城市林泉”的清幽。
就像摄影记者蔡小川在那期的封面照片中呈现的——一个穿纱裙的小女孩立在耦园的水阁望出去,水阁的花窗将对面的水面和假山景致借进来,从中可见传统美学中的对称、因借、山水关系等手法运用的精妙。但严格说来,这一景观并不“真实”。且不说蔡小川拍了几小时才等到了这个小女孩,而且照片在做后期时还PS掉了对面假山上的游客,以及小女孩身边的杂物,这在编辑部内部也引发了争论。回头去看,留下来的部分更有持久的价值,正如我们在封面标题中对园林的定义——“中国人的桃花源”。
最初我对这期“封面故事”的构想,是去寻找“活的中国园林”。这个问题的由来,是如今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园林已经异化,从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景点,如盆景般散落在城市里。游人不断地涌进来,带着一种猎奇心态漫游昔日的世界,短暂而快速地与园林发生关系。因此,我想要探究,园林只是城市化中的盆景点缀吗?一个臻于顶峰的古代文明,与当代生活有什么关联?
在探访苏州园林的几个月前,我因为采写年逾百岁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封面故事”,刚刚来过一次苏州。当时寻访的线索一是贝氏家族的远亲,另外就是与贝家有关系的园林。苏州“一城半庭园”的说法并不算夸张,最盛时城内的园林有270多座,其中53座保存至今,而去年正好是苏州园林“申遗”成功20周年。但在那一次,我已经感到这些围墙里的园林和围墙外的现代城市的割裂。城市在努力追寻它的往昔,借用一些粉墙黛瓦的仿古建筑,甚至是园林造型的公交车站,这种刻意的符号化反而不伦不类。
在贝聿铭第一次从美国回到家乡的1974年,这种断裂感肯定更甚。名园狮子林在民国时期被贝聿铭的叔祖买下,这里曾是贝聿铭的童年乐园,园林也成为他日后重要的灵感来源。我们找到了如今在苏州的贝氏家族中辈分最大的贝织芸,她曾是中学老师,退休后住在单位老房子里,家里的陈设十分简朴。贝聿铭70年代回国时,她并未见过。贝聿铭本人一直与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想象,他时隔40年回到中国时见到变为公园的狮子林、见到远亲们的复杂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跨越了40年的中西文化差异,贝聿铭更能意识到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这种断裂。所以他在苏州政府90年代起请求他为家乡设计一座标志性建筑的时候,提出了先让政府把运河清理干净的条件。到了2003年,他决定接下与拙政园一墙之隔的苏州博物馆设计时,并未像香山饭店那样给出一个众人预期的“传统”园林,而完全是一个几何造型的现代建筑。苏州博物馆对于现代建筑和历史传统之间联系的探索,对于中国本土语言的路径开创,至今仍有争议。
7月份再回到苏州,我和搭档蔡小川先去拜访了画家叶放。他的家,在市中心的十全街南石皮弄,网师园隔壁,是隐藏在联排别墅院墙里的一处当代造园。白天,坐在叶放家的厅堂中,他放下落地窗的竹帘,遮挡了阳光和暑气,也让园景变得影影绰绰。傍晚推门进园,则可以体会“不出城郭,而获林泉之怡”的私家园林意境。去叶放家不只为看园,更是因为,他和“南石皮记”是进入苏州园林体系的一块敲门砖。我们听叶放讲述他8岁之前在外高曾祖兴建的毕园中的生活记忆,从书条刻石里认识“苏黄米蔡”,从外婆的生日堂会上偷听“鸡——鸭——鱼——肉”般一波三折的昆曲吟唱,还有隆冬时节外公召集小孩子们进行的“折梅”游戏,这些是他最初的文化和审美教育。
我们还参与了叶放园林中的一场雅集。当天正赶上荷花生日,他要办一场访荷雅集。他提前两天就一直在观察荷塘里的荷花,要选那种初开的,做明清文人记载的莲房茶。雅集的程序十分繁复,包括跟荷有关的器物把玩、宴饮会意,还有宴后兴境,由曲家吟唱,琴家操执,客人们吟诗作对……叶放说,这还只是象征性地重现了雅集的一部分,而且,荷花生日只是个借口,就是借此去唤醒生活里的仪式感。
雅集中的无限可能让我更加体会到,园林不是一个空壳,不是一个艺术装置,而应该是四时晨昏的情境变化,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生活方式载体,是一个活物。但是,这种园林生活经验已经少有人懂得,在苏州,“南石皮记”几乎是一个孤本。而即便是叶放,除了在客厅与园林中对于传统近乎虔诚的再现,其他空间的陈设也十分普通,他和家人也并不能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传统中。后来还听说,这个难得的园林是打通了联排几户人家的前院而建的,因为某户的房产即将易主,院子的用途和归属也起了纷争。
叶放的园林像是众多苏州古典园林的一个隐喻。回想我们在苏州园林的那些天,白天日照太强,于是申请傍晚进园拍摄。那时候游人已无,暑气消散,可以安静地独享一园风景,才真正体会到城市山林的感觉。只是急坏了看守人,一迭声地催促,说园林里不能开灯太久,因为都是木建筑,容易引发火灾。可见园林在城市里的可游与可居,也是一种奢侈。
这些具体可感的断裂感也让我们去寻找“活的中国园林”的想法更加迫切,也更为必要。园林里是不是还有生活?还有哪种生活?将古典园林带入现代生活,是采取贝聿铭苏州博物馆式的观念连接,还是需要更长期的内化?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24个推荐 粉丝1344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