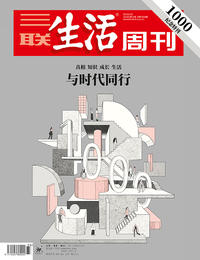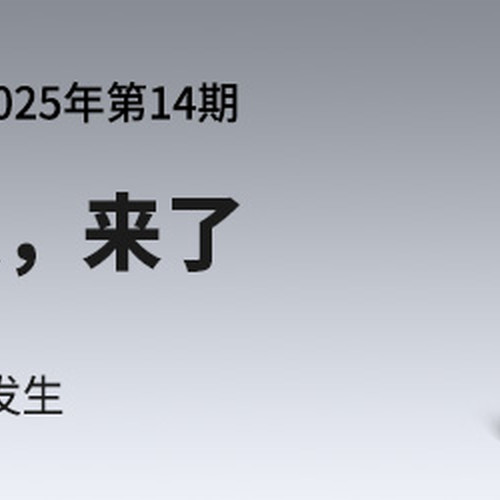悲悯与尖利:残缺带来的力量
作者:吴琪
2018-08-16·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031个字,产生7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直视最深的恐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对死亡的准备。但是在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氛围内,我从未想过,医学与死亡会成为我做报道的题目。我在其中看到一组组充满张力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病痛与健康、治疗与放弃、与死亡怒目相向还是握手言和……
2016年春天,当我走进北京的癌症病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它不像我以往的选题操作,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矿难空难事件、法律案件、学者访谈。我提出医生的选题,是因为读到美国叙事医学倡导者丽塔·卡伦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医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界”里,在学术理想、科学上的竞争压力、职业的优越感和表现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医学的主要目标——服务。而患者处在一个“生活世界”里,他们喜欢絮叨疼痛,计算看病的成本,对冷冰冰的医学名词和治疗手段感到恐惧。医生所处的“科学世界”与患者的“生活世界”造成了鸿沟,急需有效的填充物。
当时中国因为几起伤医事件,医患矛盾成了热点话题。多数人都有作为患者的经历,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不愉快的就医经历代入事件,在讨伐医生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共鸣。丽塔·卡伦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在一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中,不是强调对立,而是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处境。医生是医患关系中强势的一方,调查记者的思路往往是去描写弱势方,但是如果我们去接近“强者”呢,会不会看到另外一种真实?
在有了讲述医生故事的动机之后,对于这个开放性的选题,我需要确定的元素特别多——舞台(具体写哪个医院的哪个科室),主角(具体写哪几个医生、为什么写他们),故事(选取主角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很快把目标定在了癌症科室,因为凭借写作者的本能,我知道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故事的戏剧性会大大加强。死亡几乎是所有事物的对立面,每个人逃脱不了的结局,当它与病痛、挣扎、救助,起伏的希望与失望深度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医生可能被看作妙手神仙,也可能被当作死亡无奈的协助者。
寻找医院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群致力于推动“尊严死”的医者。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浑身插满仪器、痛苦不堪地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困惑。医学在技术至上的胜利过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缺乏人性的死胡同。他们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曾读过的《面对死亡的人》,作者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到,传统农耕时代的死亡是“被驯服的死亡”,而在医学主导下的死亡失去了自然性,反而被他叫作野蛮的死亡。
我穿梭于北京陆军总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提倡“尊严死”的医生们,发现这些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群体,反而是较早对医生沉入技术狂欢产生质疑的。他们是医生群体中的少数人,虽身披白大褂,但是试图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里自由穿梭。这些“局内人”的质疑,比一般患者对医学缺乏人性的简单指责,更加让人感到震撼。
我在中国医生的病房里,看到他们对坦然面对癌症、细心安排生活的患者暗生敬佩;对生命末期的病患们,他们向家属婉言相劝——放弃治疗、平静接受人生终点,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选择。
怎样的死亡才有意义?怎样的死亡值得提倡?医学在技术无能为力之处,如何表达它的抚慰?病痛和人生终点,难道对于一个人毫无价值吗?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它们带来的另一层意义?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思索的话题。只是当这些问题由精于延长生命的医生们来提出,别有深意。
这一次的采访,于我而言开创了操作稿子的一种新范式。过去做社会新闻,总是强调一头扎进田间地里,采访对象说什么,我们就记录什么,认为“有啥说啥”才叫真实。但是这次面对医学、死亡、医生这样拥有好几个层面的开放话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纪录片导演,采访和策划对于我来说都变得重要。
在采访的三四周里,白天跑医院、采访医生必不可少,同时我找来十几本叙事医学、临终关怀的书,有空就读。我发现从三四十年前开始,欧美就有少数医生、医学院教授反思医学至上,反思缺乏尊严地在抢救室里死亡。他们开始思考,医学如何在取得各种重大突破之后看到自己所不能?医生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在谦卑照料中寻找到力量?这些思想,放到今天医患矛盾紧张的中国,难道不同样直指我们的社会之痛吗?阅读书籍使我头脑里有了一张网格,而之前多年做社会新闻的经验,使我能迅速判断其中有价值的观点,并且意识到它们与我白天在医院里采访到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连接。
提倡“尊严死”,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医生的认知,这背后是对人性深切的尊重。即使不是面对死亡,就一般病痛而言,病人将身体和疾痛展露给医生,医生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托付?少数“局内人”的反思,使我看到了医学在走向技术极致之后的回旋,这种回旋托付到了具体的医生群体,既给了我们探讨问题的空间,又有了活生生的情感。
在我试图探讨的话题背后,有着更大的社会背景。如今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占世界的1/4,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被迫卷入了这场人生倒计时的抗争。一个人被确诊患有癌症时,这是一个让亲人痛苦和茫然的时刻:该不该如实告知病情?怎样安抚病人的情绪?怎样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当死亡不可回避时,如何面对?而作为病人,既要接受身体逐渐丧失功能的打击,又要调整和安抚自我的情绪,在技术上与疾病对峙,在心理上反而逐渐与之亲近。
在采访现场,我的情绪总是相当理性。可是一旦卸下职业的硬壳,每天采访结束后,回想起医生给我讲述的难忘的病人故事,或者是病人对自己愿望的表达,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人都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人生最终幽暗的那个深洞,我并不想现在就去凝望。好在职业身份暂借我一层坚硬的外壳,在写作思路的推动下,我像一个搭建楼房的建筑师一样,专注于寻找我要使用的各种材料。先找来大块的不同质地的材料,然后剪裁加工,探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技巧以及作品最终呈现的形态。
如何让自己有感触的主题,能够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从阅读节奏、叙述口吻、故事设置、情节推进、认知展现各个方面合而为一,对我来说,医生主题的文章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文章作者


吴琪
发表文章49篇 获得51个推荐 粉丝1615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