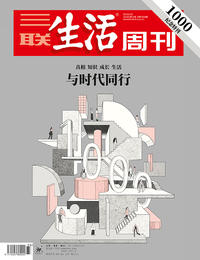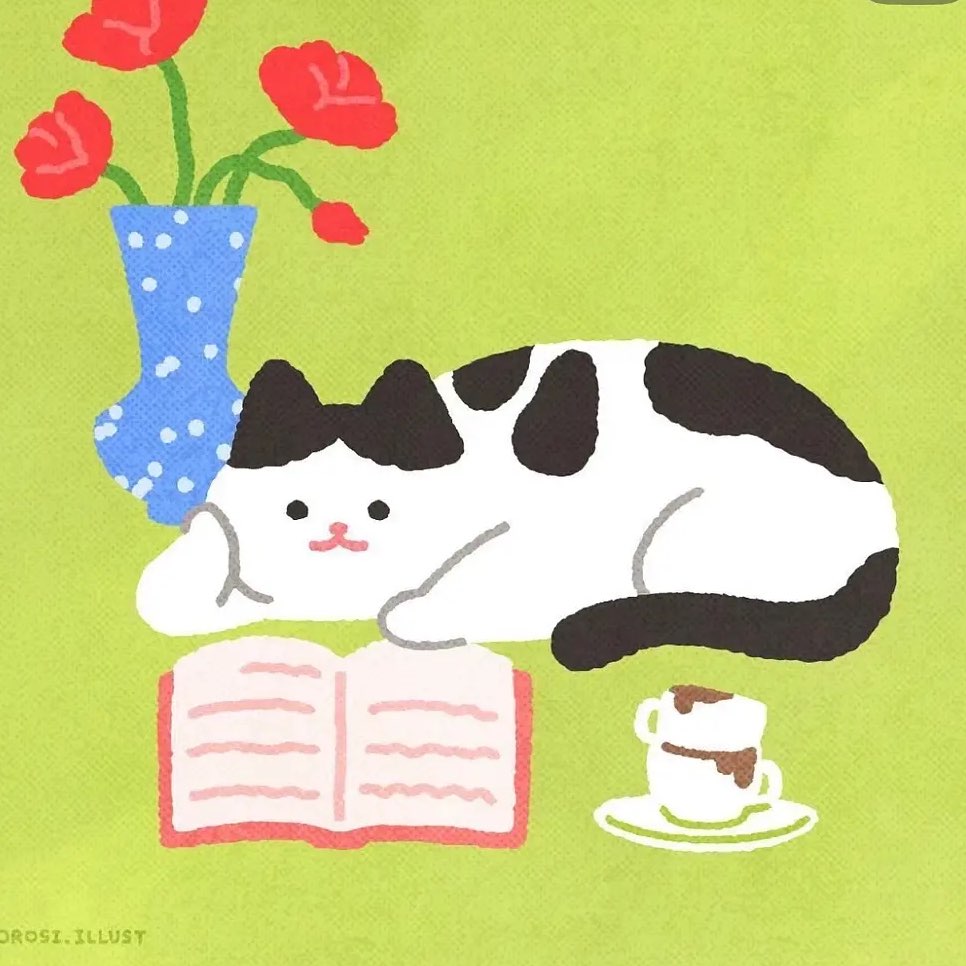不能放弃的现实主义
作者:李伟
2018-08-16·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534个字,产生8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平行世界
2000年的7月份,我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做社会记者。三联的记者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前者有固定的报道领域,而后者没有。我就是那种“非专业”的社会记者,只要是热点的选题都会去做,有时候需要上山下乡,有时候要正襟危坐,有时候去调查,有时候去“跑会”,什么事都力图了解一点,各种人都要倾听。
最初的时候,我把交换的名片收集在一个空的月饼盒里,很快就装满了。后来我用了专门收集名片的盒子,但很快也被填满。最后,我每年整理一次名片,都塞在单位大信封里。更多的人没有名片,他们的联系方式被随手记录在各种本子上。
这些人的故事有的被写进了报道,有的还潦草地停留在记录本上,还有些留在记忆里,仿佛进入到了一个个单独的隔间里,彼此不再有联系。他们的面貌林林总总:股海沉浮的基金经理、大火后失去孩子的父母、踌躇满志的海军军官、沉迷网络游戏的城市少年、贪污过亿的官员、“血汗工厂”里的“90后”、少年成名的创业者……有人在时代的列车上飞速前进,有人则被甩下来茫然四顾,还有人似乎走错了方向。
2000年开始工作,我所感受的这近2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便是分化,抑或说是阶层分立,并由此引发的观念/生活方式的冲突。买房和没买房的,一线城市与四线城市,在富士康工作的与在腾讯工作的,看中医的与看西医的,看原版迪士尼动画片与看国产“光头强”,用“小红书”与用“拼多多”,喝星巴克与喝精品手冲,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
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平行世界。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平行的。正是这些平行的世界构成了我们今日中国的面貌:多层次、多维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梦想,众声喧哗。
我常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鲁迅冷冷地说:“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很难彼此理解。共识——恐怕是今日社会最稀缺的要素。但缺乏“共识”并不可怕,毕竟共识不仅是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因此形成共识的过程才更重要,它是利益博弈,是彼此认知。而认知又是博弈的前提。可怕的是,技术进步使我们的联系越来越便捷,但“认知”的鸿沟却在被拉大。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度丰富的年代,但我们未必能正确拥有这些信息。科技公司在算法的世界中,炮制了一个个“信息茧房”,让我们只关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或者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像一个喜欢吃肉的胖子,他被推送的食谱里永远不会有蔬菜;一个只钟爱玫瑰的姑娘,会忽视掉整座植物园。越开放越封闭,越多元越孤立,既丰富又匮乏,是这个时代的悖论。
还好我们做了一本杂志,而且已经做了1000期,试图把那些时代碎片拼接起来,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接近真相,并眺望未来。我在这本杂志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建立认知,在时代的大网中梳扒珠玉和尘埃。把这些平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认识一个相对完整而真实的世界。
在认识论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终究仍有许多盲区我们未曾了解。但行至水穷处,便又想起鲁迅的另一段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终将要为他们画像,也是为时代画像。

我们的文化中,本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孔子那里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司马迁那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现实主义是对现状的勇敢回应,是对每个人的关怀与责任。而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多背离现实主义,言不由衷,沉溺于无根的虚幻中。
生活于社交媒体,则易陷入无端的狭隘,见自己难见众生。回顾这1000期的工作,我打捞起了3个人物,曾经采访过而未曾忘记。放在一起,重新讲述。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被裹挟着前行。我想,现实世界与我们的关联,之于我们的意义,便是由那些不同人的命运所体现。今天,我们不能放弃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
校长
我时常想起边疆小镇的校长张延成。他的身高有1.8米多,体格壮硕,多年的高原生活,脸被晒得紫红。在操场上,站在一群孩子中非常显眼。他是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中学的校长,新疆伊犁人,1989年毕业于新疆教育学院,然后回伊犁担任了4年的代课教师。1993年,张延成来到塔什库尔干中学任教,一人独自讲授所有的理科课程。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09年的7月,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6年。
塔什库尔干在中国最遥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的深处,塔吉克族的聚居区,毗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玄奘取经的时候曾经路过这里。除此以外就是贫瘠,一年四季遍地风沙,农作物只有土豆和一种叫恰麻菇的高原蔬菜。2009年夏天,我因为写一篇新疆的考察报道,一头扎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别的校长关心的是教育、升学率和教学负担,而张延成发愁的问题还是吃饱饭,或者说是营养问题。我见到张延成时,正赶上学生的晚饭时间。
学生们排着长队,每个人可以在门口领两个小个的油馕,然后到后面盛一碗奶茶,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领到食品的孩子,用油馕蘸着奶茶吃。“馕可以管够,就是没有菜吃。”张延成撕开一个馕递给我。早上,学生们也是吃奶茶加馕。中午会吃得好一些,一、三、五吃手抓饭,二、四吃拌面,周六、日吃馍馍菜。
学生能来上学已经不错了,家庭大多负担不起吃饭钱,于是学生们的伙食费由政府的财政负担,每人每月95元是当时这个贫困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算下来,每个孩子每天只有3.5元,只能吃3个馕和1个鸡蛋。而外面运进一棵白菜的价格也是3元多钱。张延成焦虑的是,怎么能保证孩子们每天能吃一个鸡蛋。不过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在学校还是比在家吃得好。
张延成还带着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开垦了100亩荒地作为农场,但由于气候问题,起不到什么作用。学生营养不良问题困扰着他。我见到了一个叫卡杜尔江的男孩,他已经16岁了,但十分瘦弱,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他的家位于昆仑山的深处,徒步进山70公里,顺利的话需要走3天。到夏天时,冰川融水形成山洪,他就回不去家了。
卡杜尔江并不是住得最远的学生,更偏远的乡村位于昆仑山腹地,那里学生的上学之路竟然长达1000多公里。他们先要翻出大山,到达叶城,然后再坐车穿越七县一市到达塔什库尔干,最快要走10天。每年开学前,张延成和县里的干部都要进山,把居民点的学生集中起来,统一带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再统一送回。
事实上,自治区镇政府刚刚拿出了6000多万元,完成了县城小学和中学新校舍的营建,两座学校是县城最坚固和豪华的建筑。这两座楼对新疆意义重大,因为有了它们,新疆终于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政府还承担了学生每年三四千元的学费。教师,是张延成另一个发愁的问题。偏远和艰苦令人望而却步,在学校教书的很多都是当地驻军的家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文章作者


李伟
发表文章20篇 获得33个推荐 粉丝532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