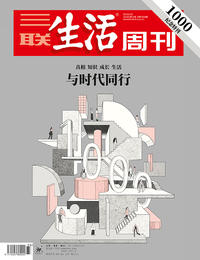丢了情节,留下故事
作者:舒可文
2018-08-16·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684个字,产生3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在媒体工作必须面对文化潮流、流行词汇,工作性质决定的。这种东西有一种强大的引力,搞不好就弄成“听风就是雨”。我喜欢读欧洲启蒙运动的书,那是他们破除偶像的时期,不是反偶像,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理性分析的手法,摆脱偶像思维。他们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破除文艺复兴运动中泛滥的文本崇拜,还有那种用“相似性”方法模仿历史和解释世界的陶醉。启蒙运动通过同一性/差异性的分析,废除了“相似性”思想方法中的大杂烩。培根按照柏拉图的四种洞穴说,拉出了四种偶像,其中洞穴偶像和剧院偶像使我们相信,事物总能相似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这个提醒特别能让人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警惕,去检查形成判断的方法。
一页记事本上记着我在读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他在文章中极力反对达朗贝尔(百科全书派的支柱之一)兴建剧院的提议,兴建剧院是为民众谋文化福利的事,经卢梭的分析,剧场里的戏剧有违初衷,剧场的存在方式隐含着一种对民众的损害:因为当它将观众引入其中,让他们心怀敬畏,坐定下来,不动不响,他们被如此地隔离和被动,就让他们失去了原来在共同体中保持的品行、行动的方向、行动的方式。他说剧院的这种特征是反社会的特征。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比之更过吧?身体面临着各种神奇事件,但意志会有什么作为?卢梭的分析当然不在剧院本身,他的论点落在:不能让舞台把人的感情带入拟像,不能让人被拟像隔离开他们自身的思想和力量。今天读来必定会反省一下,你是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剧院、美术馆,或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粉丝不计。
我们似乎都学会了政治正确地抵制强制性权力,抵制它伤及我们的权利。而流行观念携带的权力其实一点也不弱,但容易被忽视,它往往以一种很“异见”的姿态、或很“普遍”的声势显得很开明,实际上它有一种更迷人的腐蚀力,腐蚀人的精神和思想动力,继而丧失行动方向。如何对付这种力量?一不留神就被卷进去,一抵制就显得很不政治正确。比如“民国”。拿“抒情民国控”和史学家的民国史料一对比,就能看出各自的标的落在哪儿,虽然都是局部信息,一个是封闭的局部,一个是可向整体连接的局部。每个流行词都需要警惕,如果认同这些词,就容易阻碍问题链的建立,而价值和意义都是在问题链中形成的。如果一个事物单独地具有价值,不是形而上学,就是骗人。
一个词,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变成一种托词,成为回避那种更基本问题的托词。标准句法是:别再说那些了,重要的是“进步”。这个宾语可以随着流行更换为“自由”“教育”,或世界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刻薄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100多年前说的,他如果活在今天会怎么说?宾语可以换上全球化、开放、多元,也可以是自媒体。换上什么词都无所谓,问题不是这些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流行地使用它会作为各种偷懒的托词。
文章作者


舒可文
发表文章1篇 获得26个推荐 粉丝127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