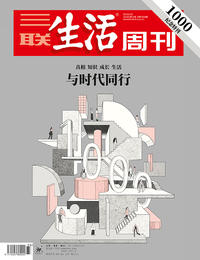开始,选择以及坚持
作者:李鸿谷
2018-08-16·阅读时长2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1357个字,产生17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2015年2月4日,离春节还有两周多时间,有点冷。
这天下午,我要去中国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报周刊参加募投的项目情况,这是第三轮汇报,也是决定我们是否中选的关键一轮。我们排在下午最后一个,4点半钟开始。上午,三联书店总经理路英勇,分管《三联生活周刊》的副总编辑常绍民过来了,他们说好了先听我试讲一次,演练之后,去集团正式讲。
可他俩真来了,议程却变了。话题很直截了当:如果这个项目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做?募投项目,可以再设计一个嘛!
这个决定我接受,没有异议。这是一个颇让人纠结的事儿,此前曾反复权衡未果。
还好,我们是最后一个汇报。虽此,也只有几个小时供我另起高楼。我们换一个什么新媒体项目?那个时候,新媒体项目,重点是好想法。
我还有什么新想法?
3000字以下的手机阅读,是信息消费,是快阅读;7万字以上,一本书的篇幅了,是慢阅读;在快慢之间,我们可否做一个“中阅读”,像我们杂志的“封面故事”一样的体量。“中阅读”,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新媒体转型。
嗯,想法有了轮廓。可是,集团总裁办公会允许我们临时更换项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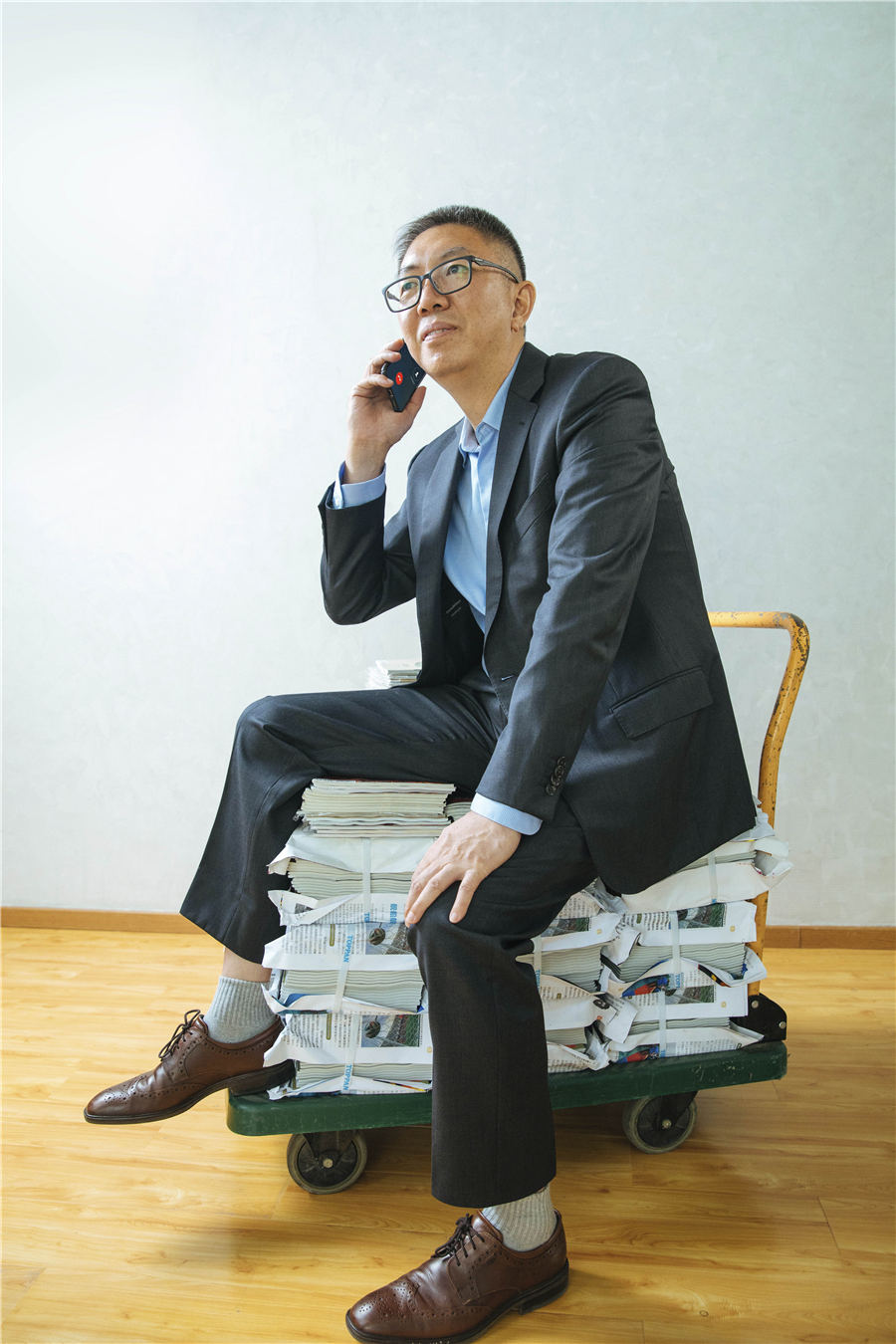
前一年,2014年,国庆节前,三联书店相关领导找到我,说周刊主编,我的前任朱伟已向店里提出了退休申请,推荐我接任他,希望我做好准备。
这年有一个系列性的变化。
早些时候,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樊希安升任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稍后,书店分管《三联生活周刊》的副总编辑潘振平退休;接着,朱伟提出退休申请……还未完,跟《三联生活周刊》合作了十多年的广告公司,之后也结束了与杂志的广告代理合同。
上级单位负责人、分管杂志的负责人、主编、广告代理公司,这一年,全换了!
《三联生活周刊》创立至今,无论以何种方式观察,2014年都是极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杂志的营收为1.28亿元,利润却达到5800万元,利润率45%。单本杂志的利润率,放眼全国,恐难有超过此数的。这是朱伟主编创造的佳绩,是一座高峰。当我接任他的位置,像他一样来操心经营工作之后,这一成绩的了不起,又有了更深的体会。
当时,没有太多时间给我感慨,有两件急迫的事情必须马上进入。
周刊的广告代理公司决定不再续约,接下来怎么办?杂志营收的关键,是广告收入。各种讨论之后,书店决定让我们自己成立广告公司。为此,多方联络我们之前广告代理公司的业务员,将大家聚集深圳,我去介绍杂志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广告公司的设想。大家还都乐意加入周刊,广告公司的老总高劲涛也理解我们的处境,未有反对,看上去一切顺利。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接到正式的通知,书店找到了新的广告代理公司,要求我参与谈判。周刊成立自己的广告公司,自然流产。后来,三联书店与这家广告公司签署了代理合同。
广告代理公司易主,带来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是三联书店下面一个编辑部的建制,并非独立法人。过去与广告代理公司合作,虽然是三联书店作为甲方签署合同,但真实的业务关系,实际是《三联生活周刊》操盘,包括催款、收款与入账种种。十多年,一直如此。而这次更换广告公司,三联书店、《三联生活周刊》与广告公司的三方关系,调整成书店与广告公司是实质性的业务合作关系,《三联生活周刊》,类似一个广告发布平台。
与寻找广告公司同样迫切的另一件事,是中国出版集团股份公司重启上市程序,我们需要设计一款媒体融合的产品,进入集团的募投项目计划。
周刊的官方微博有1000多万的粉丝,微信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但这两个加起来,作为募投项目,还是小点。找来微博微信的经营负责人、发行总监张薇,我们讨论设计了一款涵盖微博与微信的新媒体产品,去集团作第一轮汇报,效果还不错,得到的评语是:这是集团最有互联网思维的产品。有了这个开头,募投项目这条路,得走下去了!既如此,必须有编辑部的同事介入,才能落实真正的媒体“转型”,以及发展“融合”。这样,主编助理吴琪调过来负责新媒体项目。
所谓开始,很多时候是情势所致。周刊的新媒体募投项目,由不得谁,必须开始!
三联书店跟新的广告公司签了一个大单,代理费比上一年度要高。在纸媒发行与广告断崖式坠落的年代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头。这个大单,我们交付的是全媒体广告代理权,新媒体广告代理权签给了广告公司。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三联生活周刊》的新媒体进入了集团公司的募投项目,集团将有募集款的投入,而广告收益却早被别人拿走了,上市公告如何解释这种投入与产出的分离?这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冲突。
而且,集团募投说明会明确指出:如果新媒体项目进入募投,在公司上市前,不可获取政府资助,也不可接受社会投资……完成上市过程,差不多得两年时间。这意味着,两年里,我们的新媒体项目,最需要资本投入的产品,却被堵死资本渠道,只能自己投资。在唯有快速迭代才能生存的新媒体时代,这种硬性约束,岂非自断生路?
在募投项目最后一轮汇报前,这种种现实困境,让人纠结再三。
如何解套?那天上午,决定明确:既定的新媒体项目自行运行,募投项目提出一个未来可随时启动的计划,两厢分离,规避结构性的冲突,使我们的新媒体可以快速成长起来。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好主意。
汇报的结果,“快慢之间,有中读”,这个想象力有说服力,“中阅读”没有被拒绝,项目纳入募投计划。此时,我们需要再投入一位专才来编纂募投计划书。这是一套格式文件,包括可行性报告、项目计划、投入规模、产出预期……把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变成至少纸面上逻辑清晰的各种数据与增长曲线,并不容易。主笔魏一平来担纲此事,应对挑战。
另起炉灶新设计的募投项目入围了,落定了。我们可控的,能够快速发展的新媒体项目也保留下来了。这个过程虽有波澜,还算是顺利度过。
稍后,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决定来《三联生活周刊》调研。有了上述结果支持,在汇报会上我提出:希望集团给予我们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包括:一、公司化;二、引进外部资本;三、员工持股。谭跃不仅认可这三个要求,更认可了周刊转型的整体性思路。同时,还要求我去集团的“十三五”规划会上汇报周刊的转型思路。规划会后,集团有同事告诉我,作为集团二级单位下面的一个编辑部,你来单独做大会主题发言,比较罕见,二级单位未必都有这个待遇,已经很破格了。
那个夏天的早晨,艳阳高照,阳光明媚,未来仿佛伸手可及。
那段时间,我们这个小团队真是干劲冲天,连轴转地拜访各种投资机构,问计各方,谋划未来我们员工持股、也方便投资机构进入的新公司架构。
一旦开始,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新成立的公司与《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关系?作为一个编辑部的《三联生活周刊》是评估作价之后进入公司,还是先成立一个方便引进社会资本的全新公司?问题很简单,却是关键的。为着《三联生活周刊》转型的新媒体公司,如果独立成立,它未来与三联书店下属的《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是什么关系?对于没有公司经验的我,以及我的那些同事们,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琢磨。
抽象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编辑部如何确位,需要有明确的答案,公司化才能够推进下去。在公司化的路途上,不止这一项挑战。我们固然可以把新媒体项目从集团募投计划里剥离出来,但新媒体产品,在新签约的广告公司看来,他们应当拥有运营权——技术、市场、渠道与运行,都应由他们来操控;而《三联生活周刊》,只负责生产广受欢迎的内容。这个想法很飞扬,但可行度有多大呢?果如此,为着转型快速发展而成立的公司,无论是何种性质,与周刊又有什么关系?
解开了旧套,新问题又涌现。所有的事后叙述,都可以条理清晰,仿佛从来如此。但回到历史现场,真实状况是一团乱麻,让人极其困扰,症结何在?出路何在?
逐渐,问题的实质显现,《三联生活周刊》是否、以及如何公司化,是纲领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独立法人公司化之后,才可能以此为根基,成立为着周刊转型的新媒体公司。上位公司与下位公司的关系,非此无法定位,这是一切逻辑的起点。否则,无论成立什么样的公司,也无论经营权归属何方,它都无法跟一个编辑部建立有法律意义的、实质性的关联。也唯有《三联生活周刊》公司化,才方便收回经营权,重组经营关系。否则募投项目的投入与收益分离状况,仍将继续。
逻辑上悖反,现实早有表现。当时一家大型网络公司跟我们谈版权开发合作,快谈到签约阶段,被对方律师叫停,原因是有风险。与《三联生活周刊》的版权合作,对方发现自己分别要跟周刊的上级公司三联书店签署版权合同,与杂志的广告代理公司签署利益分配合同。真正的版权方,对方实质性的合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成了没有任何权益的第三方。如此这般,何以转型?融合什么?
千难万难,必须从《三联生活周刊》的实体化起步,任何苟且,去不到远方。
问题症结既已明确,行动当有方向,但现实却出乎意料。周刊的新媒体项目,经过集团几轮论证认可,被大家看好,所以拿回来自行经营,希望它快速成长。开始上级口头应允了900万元的投入,之后降到260万元——这是之前周刊向新闻出版总局争取的转型资助款,钱到账两年后,可以名实相符地用于周刊转型了。可是,兴奋不能来得太早,我们相关项目的运行计划报上去后,得回明确的答复:新媒体项目所有支出,停止!
为什么?集团二级公司的投资,是要挤占公司当年利润的。而考核并决定集团二级机构负责人业绩的,不是是否开始媒体融合,而是利润指标是否完成。这样的制度安排,新媒体转型即使急迫如火,从制度条件来看,无法投入!
不处于问题核心地带,难以理解矛盾纠缠的实质;但真正进入冲突的枢纽,压力之巨,才是真实感受。矛盾交集,那年年中,张薇辞职离去,下半年,吴琪也托人相告:计划辞职……

为了写这份回顾,我翻了2015年至今的每年第一期杂志。版权页上主编、副主编、主笔、记者(包括摄影记者),2015年第一期登录的采编团队有60人,一年之后,2016年第一期只剩下51人,进进出出,净流失15%,其中副主编、资深主笔与主笔,关键中层的流失,占2/3。
辞职,人才流失,无法制止的流失,带来了整体士气的颓唐,我们还有未来吗?悲观在漫延。
如何提振士气,减缓杂志衰势,争取下落速度比行业慢一些……日常性的焦虑很折磨人。
发行部同事告诉我,说我们杂志的印厂负责人希望来拜访。我问了一嘴,杂志的订价什么时间截止?答案是调整价格7月底必须报邮局。嗯,我们还有时间。北京利丰雅高的负责人郭健拿来一整套压缩成本的方案,这些都已经被我们的同行采用,包括降低纸张的规格、减少页码……算下来,我们一年可节省100多万元。在讨论中,我说,既然可用节省的方式来应对下滑、获取利润,为何不可以试试杂志的定价上涨呢?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郭健的诧异表情,他顿了顿,严肃地说:如果选择扩张,方案必须重新调整。
即使颓势,即使所有人采取消极的防守策略,我们可否反其道而行之,选择积极的进攻之道?至少,可以想象一下嘛。
各种喧哗声中,纸媒从业者的悲观情绪被完全鼓噪起来,动辄抱团取暖,仿佛末世来临,真实的杂志下降,远远没有士气下落的速度快。想象的危险,总比真实的危险让人恐怖。所谓衰世,大概是指这种情绪大于事实的状况吧!这是可怕的。
一念既起,当然前行。发行部同事计算后告诉我,如果周刊从每本12元,提价到15元,只要订阅能够达到上年的80%,营收就能持平。如果收入持平,这是底线,我们的进攻策略就能奏效,可以收获士气,减缓悲观氛围,甚至跑过大盘,少输当赢。
如果选择进攻,与节省成本的办法一样,也需要完善杂志整体应对方案。即使杂志的广告从过去平均每期30多页,减少到十几页,杂志的页码仍不能减少;同时,必须调整规范编辑记者的薪酬标准,不是减少而是提升。进攻之道,是系统性的安排,绝非一个姿态。
可是,纸媒全面的衰退,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用进攻策略来对抗颓势,挽回自信,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年订阅量急速下落,达不到上年度订阅量的80%,全盘皆输。
我们,还有胆吗?
文章作者


李鸿谷
发表文章26篇 获得88个推荐 粉丝1239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