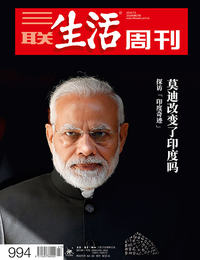莫迪改变了印度吗?:探访“印度奇迹”
作者:刘怡
2018-07-04·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201个字,产生14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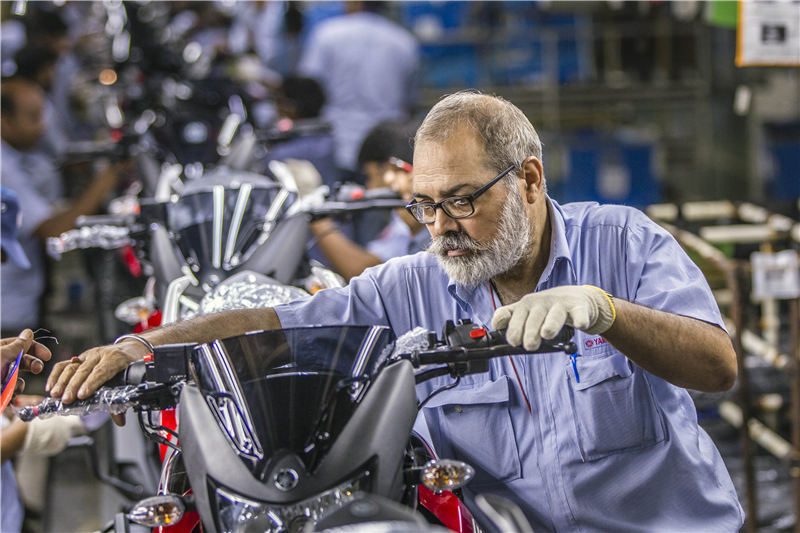
1962年,29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维蒂亚德哈尔·奈保尔(V. S. Naipaul)偕妻子离开伦敦,踏上前往印度的寻根之旅。在那之前,他对这片遥远大陆的印象完全来自童年时代外祖父的只言片语: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中存在一个巨大而朦胧的神秘国度,那里有着自洽的、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原生宗教,并使它的万千子民永远带上了一种特立独行的烙印。尽管这种杂糅有想象的记忆终结于19世纪末外祖父迁居英属特立尼达的谋生之旅——那个加勒比海岛国也是奈保尔的出生地——却使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始终无法回避“‘我们’与‘他们’(周遭的加勒比海土著及其英国统治者)有何不同”以及“我从何处来”这两大终极追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在奈保尔身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归乡”,似乎成为一剂最终解药。
从那时起直至1988年,奈保尔在超过1/4个世纪里数次游历全印度,写出了被合称为“印度三部曲”的三大本长篇游记。在《幽暗国度》(1964)中,关于血缘和精神故乡的浪漫想象已然被巨大的幻灭感所取代,作家看到了一个丑陋、浮夸、挣扎在后殖民时代泥潭中无力自拔的现代印度:陈腐黯淡的旧传统与殖民统治残留的形式主义夹杂在一起,使次大陆的每一个个体都呈现出荒诞可悲的精神状态。《受伤的文明》(1976)则开始咀嚼20世纪印度的政治失败,一度被奈保尔尊敬、崇拜的甘地被证明依旧无法摆脱印度教教义对内在世界的痴迷以及拒绝正视现实世界的盲目,结果遂使对往昔乌托邦的痴迷和自以为是的傲慢被等同起来,最终造成了国大党(INC)的治理赤字:这个自诩缔造了现代印度的政党,竟只能靠宣布紧急状态来维持地位!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33个推荐 粉丝2498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