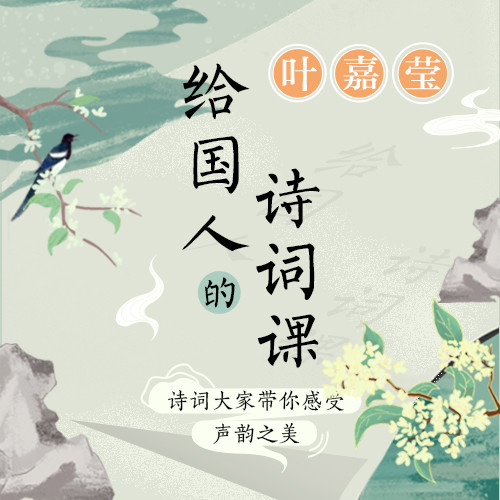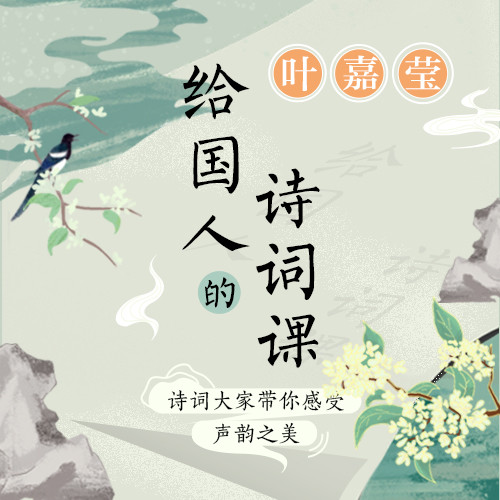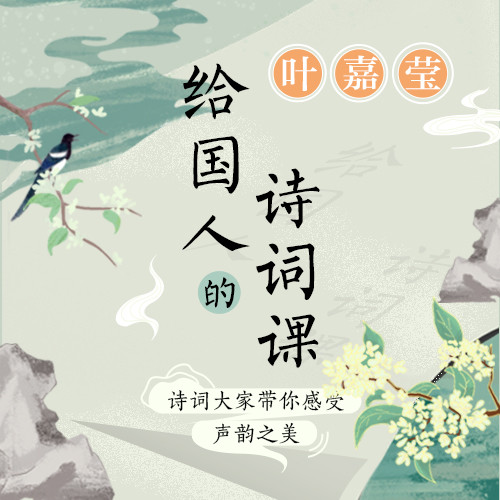摩羯罩命与春梦婆娑:苏轼的忧患与超越
作者:独芒
2017-08-18·阅读时长14分钟
说起东坡居士苏轼,大约略读过中国书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即使过去没有受过教育的所谓蚕妇村氓,讲起苏东坡的趣闻逸事,也往往头头是道,例如传说中他的小妹三难新郎而他暗中解围之类。此外如拜佛修禅的僧俗两众,常常拿苏轼和好友佛印禅师打的机锋来参话头;饕餮之徒,则至今闻东坡肉而垂涎。似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巨匠当中,苏轼是很难得的让三教九流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到亲切的一位,他的声名也流传得特别广泛而持久。从严肃方面说,他在生时不仅雄视一世,为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坛祭酒,而且北边的辽国、朝鲜、日本,南边的越南,都推崇他的文字,可以说是泛东亚的偶像。他的作品不仅广泛地流传,并且吸引了许多人来研究和揣摩。仅就诗歌而论,则北宋末便开始有人来作注解,到署名南宋王十朋编注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罗列出的给苏诗作注的人士就已经有九十余家,从那之后到如今,研究者更不知凡几。自通俗方面而言,苏轼近千年来始终是大众津津乐道的人物。象早在宋代出现的佚名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就已经兴致勃勃地编排起苏轼前生的故事和转世后的因果。发展到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当中,每一部都收录了与苏轼相关的故事:《喻世明言》里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便是直接承继《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而来;《警世通言》里,则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把历史上新旧两党的政争,改头换面为两位文豪之间逞才斗智的公案;在《醒世恒言》里,苏轼又是“苏小妹三难新郎”和“佛印师四调琴娘”两篇故事里的重要配角。此外如元之杂剧,明清之传奇,也有不少有关苏轼的作品,象元剧里的《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明传奇中的《赤壁记》、《金莲记》、《狮吼记》等等,林林总总,而今或存或佚,一共不下二十余种。
东坡家喻户晓如此,现在我又来谈讲他的诗词,恐只堪覆瓿耳。但仍然来写这篇文字者,是因为有一种私见:积淀在大众记忆中的苏轼,往往或者是洪才河泻,下笔龙蛇飞动的文豪,或者是超然物表,与清风明月同归的谪仙,又或者是滑稽突梯,善言能谑的喜剧性人物。凡此种种,原并不错,但似乎都有意无意忘却了苏轼还是一位仁民爱物的儒者,一位有抱负而始终未申的政治家,一位曾在历史的风涛中历经颠沛、几度近于灭顶的幸存者。他在咏杜甫的诗中曾经感叹:“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这实际也成为他自己的写照。我们读东坡的诗词,不应忘记他与现实紧密的关联。体味他如何在横逆之际努力摆脱生活的缧绁而追寻精神的自由,又如何在淡泊的文字中暗自坚守个体的意志以傲视不公的命运,这不仅有助我们从学术上对苏轼有一完整的了解,更可以启发我们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荆棘与荒芜。
从这一角度阅读苏轼的诗词,最好还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按照编年的顺序。苏轼一生,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早年游学与游宦;(二)“乌台诗案”与流放黄州;(三)元祐初年短暂的苏息;(四)再度流放惠州、儋州,以及晚年北归和谢世。早年游学与游宦,是苏轼平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代;而他遭遇挫折的岁月,却又往往是他在文学上成果丰硕的阶段。苏轼晚年曾感喟:“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正指此而言。故此,下文的介绍也特别集中于第一、第二、第四等三个时期。
早年游学与游宦: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公历1037年1月8日下午6-8时)。他的生日与生时,说来有一种有趣的巧合。依照公历计算,他的生日固然落于十二星座的摩羯座中;而按照中国古代的星象学,他出生的时辰同样属于摩羯宫。在古人看来,摩羯宫似乎是个不太吉利的星座。苏轼后来曾感叹:“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东坡志林》)。但是,他的少年和青年岁月,还是十分顺遂的。他在七八岁时正式开蒙,很快展露出文学的才华。二十二岁(按:本文所说年岁,统指虚岁)时他中进士,文章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激赏。二十六岁,他又应制科,被评为三等,但第一、二等照例永远空缺,所以实际是中了头等。同年他正式踏入宦途,在陕西凤翔为官,一时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了。不过与弟弟苏辙的分离,却引发他的思念和慨叹。这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兄弟二人在郑州西门作别。随后,苏轼尚在旅途中,二人便不断相互写诗赠答。下面这首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便是苏轼行至渑池时写给苏辙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在虚实之间游走自如,既表达了对幼弟的思念,更感叹了人世的无常。苏轼、苏辙兄弟早年赴汴梁途中曾途经渑池,借宿县中佛寺,并在寺壁题诗。如今苏轼故地重游,人物俱非,故有后二联之叹。但全诗劲拔之处,尤在于开首四句。在首联中,苏轼以飞鸿踏雪的明喻比拟人生,而颔联又贯通直下,延续这一比喻,给予其更为详尽的拓展。运用具体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对抽象的、本来难以琢磨的思想和情感,这在他人为难,而对于苏轼来说却正是拿手好戏。他的才华涌溢,有时几乎不择地而出,诗成之后,令人读来一气呵成,似乎毫不用力,但回头仔细思索,又不能不惊叹于他构思的新奇和精确。不过,初识愁滋味的苏轼此时却不会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对他而言才刚刚开始。
在此后的数年中,苏轼因父亲的去世回乡丁忧。当他重新踏入官场时,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的神宗皇帝信用王安石推行新政改革,而苏轼对新政则有许多批评的意见。因此之故,他无法在中央政府立足,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辗转任职。但是,未曾遭受过太大挫折的苏轼此时依旧是积极入世的、意气风发的,甚至是天真烂漫的;在忠实履行职责的同时,他继续毫无顾忌地挥洒他的笔墨,于是我们便得到许多传世的名篇。例如,在杭州时,他在望湖楼上醉兴淋漓,写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其一)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其二)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其五)
在他的笔下,西湖的阴与晴、动与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发生急速的转换。本来任运无心的自然与湖山怀抱中的往来人物,也变得浑然一体。随遇而安的诗人在宦游的漂泊中安住,内心的安闲和山水的嘉美同样形成完美的契合。在密州,他的豪情大发,于是有《江城子(猎词)》之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诗人真是张扬极了,得意极了;这种放纵的豪情让我们想起盛唐。放纵在此绝非意味着末世的烂熟和颓废,而是蓬勃的生命元气不可抑止的迸发。而苏词中的双璧之一,《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也是密州时代的成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后人赞叹这首词作,说它“有仙气缥缈于毫端”,“大开大合之笔”,“格高千古”。瑰丽的想象,俊伟的笔锋,开阔的胸襟,共同熔铸成这首宋词豪放派的经典。
苏轼常被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开辟者,其实豪放一词并不能笼罩他作品的全部。就词作而言,他同样可以谱写出缠绵的、哀婉的,乃至凄楚的情调。例如《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一首:
去年相送,馀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这首作品采取闺怨诗的风格和角度,又化用了《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境和笔法,却非单纯的模仿。杨花似雪,游子不归,单人只影,对月独斟,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文字,一种离情别绪,扑面而来。而在密州时做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首,更是古今悼亡诗中的铭心绝品: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徐州,他追记与友人游览百步洪时的情景,作《百步洪》诗两首,极文字穷形尽相之能事,在此举一首为例:
其一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接连用六个比喻刻画河水的湍急和一叶轻舟在水上漂流的迅捷,笔锋所至,真有令人瞠目屏息之效。而诗后一半,笔锋转折,诗人从“险中得乐”的刺激中超拔而出,忽然作出世想,正如禅宗公案,翻下转语,最终归于无言。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加险恶的政治的漩涡,正在前面等待着苏轼。
“乌台诗案”与流放黄州: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批评新法,遭当政者罗织入罪,几遭不测,史称“乌台诗案”。在各方营救之下,最终以贬官黄州了结。元丰三年阴历正月初一日,苏轼在御史台官员的押解下,奔赴黄州,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流放生活。初到黄州,他的心情无疑是恓惶的。但是艺术家不可抑止的创作欲,仍然驱使他很快重新提笔。《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词,很能作为他惊魂初定时心灵的写照: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然而诗人乐观旷达的心性很快让他从惶恐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初到黄州》一诗,便反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声: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是自嘲,也是自解,同时还有一分隐约的傲岸。艰难的流放生活,在诗人笔下充满田园乐趣;仕途的巨大挫折,被诗人看作古今艺术家共同的遭遇。作为有罪之身,诗人口头上极度的谦抑,其实又何尝不是对当权者淫威默默的挑战?无论是放达,还是倔强,都是苏轼对抗命运的武器。他终究是不肯被命运击倒的。不久,苏轼又写下著名的诗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从中不难看到诗人卓然挺立的自我意识: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黄州流放,是诗人生活的低谷,却带来了他创作的高潮。政治,他是完全无份了,但他由此反而可以用全部的身心热情拥抱自然,在清寒的日常生活中缔造艺术,以精神的自由对抗现实的拘束。从寄居定慧院到躬耕东坡、营建雪堂,从闲步江城、漫游村落到泛舟赤壁、寄啸山林,苏轼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灵感俯拾皆是的境界。旅途中醉卧路边的一场酣眠,偶遇的一阵急雨,都能触发诗人的天机,造就仙风缥缈、理趣圆融的词中妙品: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西江月》中诗人在一夜酩酊后醒来,展开惺忪的双眼,便与晨光里静谧无声的自然美景猝然相遇了。他惊喜地发现了美,也似乎体味了一种存在的大神秘。在极静之中的一声鸟鸣似乎打破了岑寂,却又衬托了岑寂;而这一声天籁,又如同禅宗的一声棒喝,把不可言说的真实妙谛呈现在诗人心中。如果说,《西江月》里,诗人怀抱一颗活泼而纯净的赤子之心,宛若返璞归真的婴孩,那么,《定风波》里的诗人,则是千峰行过,摆脱了个人休咎悲喜的烦扰而直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智者。无论自然或人生路上的晴雨晦明,在他眼中都无分别,也不能令他扰动;而这番洞彻,却又不曾令他陷入虚无,反而使他吟啸前行的步履更为坚定。这种对人生的体味,亦禅、亦道、亦儒,而各有所取,总归作者一心;苏轼的心灵,在苦难的磨砺和艺术的抚慰下,更加成熟了。
黄州时代苏轼文学创作的极峰,应属前后两《赤壁赋》和词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了。限于篇幅,前者姑且不论,而后者传唱千古,堪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列为苏词的双璧: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是后人叹为足令“江涛鼎沸”的伟词。百余字的词作,却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曲般气概非凡。宏壮的起笔奔流直下,奏响这交响的主题,连同随后对古代雄杰伟业的遥想追述,真有扛鼎之力;诗人的精神随同自己的想象,超越时空的局限,与古人遥相呼应,成就一场慷慨淋漓的兴会,演为激昂澎湃的乐章。而纵然时光的冲刷不免令古今豪杰先后逝去,词章的结尾在感喟人生如梦时,却没有衰飒和颓唐;在文字戛然而止后,我们似乎依旧可以听到袅袅的余声。
“兹游奇绝冠平生”:
公元1085年,宋神宗赵顼去世,年幼的宋哲宗赵煦继位,次年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当国,政局为之一变,苏轼的处境也大为改观,曾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但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再行新法,苏轼等旧臣又受到迫害。在此后的六年中,苏轼屡遭贬谪,先后被流放至今天广东的惠州、海南的儋州,漂泊至天涯海角。但他虽身处逆境,仍然保持旷达的胸怀。在这一阶段,他的诗风变得更为淡泊,企慕晋代的陶渊明,时时遥隔时空写诗与陶唱和。同时,也许因为诗人毕竟已到暮年,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生空幻的把玩和歌唱增加了,而态度也变得更加随遇而安。在他流放儋州时,偶遇一位七十岁的老妪,对诗人说道:“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深以为然,而这位无名的老妪,也就此在文学史上留下“春梦婆”的雅号。然而这位春梦婆实有其人耶?抑或东坡居士自弄狡狯耶?春梦婆娑,安知其是耶非耶?
论道东坡的旷达,可以先后在惠州、儋州以《纵笔》为题的几首七言绝句为代表:
纵笔(按:作于惠州)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三首(按:作于儋州)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但他埋藏在心底的深愁,却也不时在作品中浮现。罪官的身份、遥远的流放,使他与旧日友朋的往来变得日益稀疏,而只有弟弟苏辙还能继续与他唱和。我们阅读《西江月 中秋怀子由》这首作于儋州的作品,再回顾青年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真不禁感慨,人生能经历多少沧桑!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公元1100年,年已六十五岁的东坡,几乎是颇为意外地接到遇赦北归的诏命。一时间,他旧日的豪气似乎又被点燃了;或者说,这股豪气实际始终潜藏在他的心底,与他恬退超然的心境一刚一柔,一进一退,成为共同支撑他生命的内在力量。读《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我们恍惚又见到了高歌“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东坡的精神依旧是刚健的,可惜,他的身体久历风霜之后,终于不能支持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中国文化史上一颗伟大的星辰陨落了。
苏轼的人生,多患难而少安乐。但他的诗作,并不斤斤于记载自己的穷愁,而始终以宏大的心胸,追求对人生的超越,这也是后世读者热爱苏轼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又不可仅仅赞叹他的超越,反而忘记诗人曾经历经的苦难,忘记他与苦难抗衡的倔强与豪迈。苏轼毕竟不是纯然出世的隐者,在他的诗章中,时刻跃动着一个蓬勃的、不屈服的生命。理解这个伟大的生命,足以让我们自己渺小的、庸常的生命获得振拔,在遍地“黄茅白苇”的荒芜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园地。
文章作者


独芒
发表文章28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96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