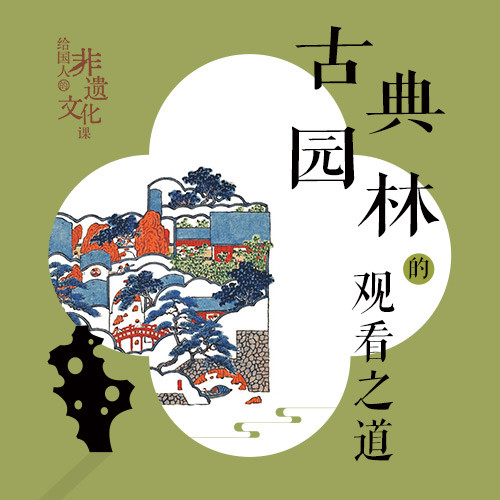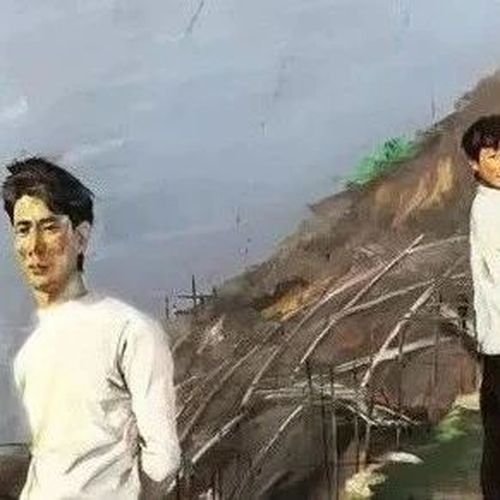慈爱的智者:纪念钱青老师
作者:独芒
2020-08-19·阅读时长8分钟
慈爱的智者:纪念钱青老师
宁欣
五月里沉闷的一天。正在家中备课,在北外任教的老同学吴樯忽然发来讯息:钱青老师于本月十七日在美国芝加哥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噩耗传来,我一时只觉胸中空荡,继而,种种细碎但鲜活的记忆此伏彼起、不受控制地在头脑中涌现:二十多年前的北外青春岁月、课堂上下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钱青老师儒雅而洞察世事的、微笑的面庞。我当时便想,应该写点什么纪念老师;但是,竟拖延至今才真正动笔。这一方面固然是怠惰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对老师一贯的敬畏让我不敢草草行事。然而心钝手拙如我,毕竟写不出高明而全面的纪念文章来,最终也只是把一些最深刻的往事的印痕努力转化为文字而已。这只能加深我对老师的歉疚。
从1993年到2000年,我有幸在北外英语系连续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位。当时英语系的老辈学者中,周公(周珏良)先此已归道山,许老(许国璋)于1994年仙逝,王公(王佐良)也于1995年辞世。我们这一辈学生,没有亲炙这些大师的运气。但三公谢世之后,北外英语系依然能雄踞国内同类学科之首,这是因为系里仍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在当时任教的老师当中,钱青老师的学术声望无疑是第一流的。不过,当时她也年过花甲,只给研究生上课,因此本科四年,我们不曾在课堂上领略钱老师的风采,只是在前辈学长的传闻中得知她的学术是何等精纯、而对学生、对学术的要求又何等严格。我们平时在校园里望见她,只见她永远是留着最简单的齐颈“学生头”发型,圆圆的眼镜片,面容严肃地独自行走,这更加深了我们对她的敬畏之心。
与钱老师直接接触,是从1997年进入本系英美文学硕士专业之后。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课上,我们先后上了老师数门课程,被老师改了我们不知多少篇学期论文;课下,老师或者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或是在平日的接触中对我们随时指点,很自然地慢慢熟悉起来,不过那份敬畏之心并未彻底烟消云散,说转化为敬爱也许更为恰当。也因为这样,我始终对老师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在美国芝加哥定居,而她在国内是一个人生活。但也许这正是师生间适当的距离。老师有时偶然提及往事,也都是与学术有关的。比如,她1981至198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攻读博士学位,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的文学学者。而这背后便有个小故事。钱老师出国学习之前,已经在北外被评为副教授,原本是要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出国到芝大短期进修的。但她清醒地认识到,数十年锁国之后,我们对西方当代学术的发展已很隔膜,对现代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更乏了解。为了充实学养、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实有正式攻读博士学位的必要。可是她一开始向领导提出这种想法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很令人无语:以堂堂中国的副教授去美国从头读博士,岂非有损国家的尊严?后来,钱老师请出许国璋教授“作保”,才得以成行。在芝大,她能用三年时间就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极了不起的;通常在美国读文科的博士,至少要五六年时间,更长的也不少见。由此可见,钱老师原本的学术积淀是很丰厚、很扎实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她读书时的勤奋刻苦。她学成后有机会留在美国,然而一拿到学位,她就回北外来了。她曾笑说,这是因为当初许国璋先生是她的“保人”,她不想给许老带来麻烦。实际上,她在美国攻读博士时,除了对自己课题的研究,早有吸取国外经验建设一流英美文学学科的理想。这些构想后来在北外英语系的研究生培养中逐步得以实现。除了全英语教学和论文写作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是从一开始就固定导师、固定方向,而是首先要上一系列研究生讨论课,全面地了解英美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以及各种文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才确定自己研究的课题,并和心目中的理想导师双向沟通、双向选择。这种方式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国内文科研究生培养的常态,但在上世纪八十乃至九十年代,却还十分新颖。追本溯源,这其实与美国研究生培养的模式十分接近。在外国各种不同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中,美国模式素来以能短时间、高效率地打造人才而著称。对这种模式或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的成效确实是非常显著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个本科毕业、各方面还都不够成熟的大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教育打下广博坚实的基础,进而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专门人才;同时,这种模式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较多、较高效地培养人才,而不是仅仅造就极少数的精英。而中国学生学习英美文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要克服的跨文化挑战无疑更数倍于研读本国文学的英美学人。因此,这种厚积薄发、密集高效的培养模式就更加适合我国的现实。我们这一辈学生入学的时候,这种培养方式已经成熟定型,当时我们也就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未多想。今天回顾起来,最初的拓荒者们在开辟新模式的时候,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钱青老师正是这群拓荒者中的一位领军人物。
读硕士的两年半里,我先后选过钱青老师三门课程:《现代美国小说》、《当代美国小说》和《文献目录学》。现在闭起眼睛,我还能回想起老师在讲桌上摊开大大小小的原著和参考书册、用纯正而典雅的英国音从容论道的场景。三门课里,《现代美国小说》和《当代美国小说》都要啃不少大部头原著,对初涉文学研究的学生而言,阅读量空前;而上课时,一面要跟随着老师的思路奋笔如飞地做笔记,一面还要随时准备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压力甚大。不过,这种良性的压力颇能激发人的潜能,而初次接触许多以前不熟悉、甚至未听说的作家作品时强烈的好奇心、以及获得新知给人带来的喜悦,都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使我们一班同学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深入文学的堂奥,在不知不觉中取得进步。记得《现代美国小说》是我上的第一门钱老师的课,而课上研读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小说家伊迪斯·沃顿和维拉·凯瑟,恰恰都是以前不曾接触过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至今我对她们的印象反而最为鲜明:沃顿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以《圣经·传道书》中的典故为题,借传统“风习小说”(novel of manners)的形式暴露纽约旧家华鲜生活背后的残酷自私,同情地描述特立独行、追求自由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凯瑟的《教授之屋》(The Professor’s House)用充满诗意的独特语言风格揭示现代社会中理想与现实、艺术与世俗的冲突,写出艺术家自身的矛盾和最终的坚守。从这些作品入手,钱青老师引导我们学习对文学文本的细读能力,也让我们开始理解何谓文学批评、什么是现代性和现代主义。随后,在这门课上,我们马不停蹄地读德莱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紧接着又在《当代美国小说》课上读《麦田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五号屠宰场》…… 钱老师的这两门课,与当时吴冰老师的《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张中载老师的《现代英国小说》和《当代英国小说》等课程相互呼应,让我们得以初窥英美小说的整体面貌。可惜的是,阴错阳差,我读研究生这段时间,钱老师自己最为得意的19世纪英国小说(或曰维多利亚小说)却没有轮到开课,真是遗憾之至。记得有一次老师和我交谈,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立时间神采飞扬,称赞他的“巴赛特郡小说”系列写得极好。我当时根本没有读过特罗洛普的作品,只能盲目唯唯。更可惭愧的是,直到今天,我也还没有认真研读过特罗洛普。今后我要补上这一课,能力允许的话,还要把特罗洛普的作品列入我自己课程的阅读书目里介绍给学生,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目录学为学术之本”,中外文学皆然。文学研究与其它任何研究一样,需要懂得如何全面地搜集和分析资料,如何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当代的学术动态;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撰写论文。钱青老师历来重视目录学的研究和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她以一人之力,著就《英美文学工具书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广泛而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英美文学领域中各种权威的文学目录、辞书、系列文学史、系列作家传记以及文学批评丛书等,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以此书为基础,老师为本专业研究生开设了专门的文献目录学课程,一面介绍各种权威著作,一面通过实践培养我们上天入地,“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能力。这门课是研究生专业课中唯一不需写学期论文的,但是期末的考核也足以让人汗流浃背。最后一堂课时,老师把我们带到北外图书馆新馆(今日恐早已是旧馆了)二楼的英语工具书阅览室,将我们分为几个小组,随机抽取题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相关的参考书,在书中找出相关的内容,最后组织成研究报告。我们同组的几个人真是象百米冲刺一样,片刻不敢耽误。好在工具书阅览室是我们常来读书自修的地方,老师介绍过的参考书,我们平时都来翻阅过,总算是都在考试中过了关。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充满欢乐的一幕。附带,北外图书馆外文藏书的丰富,也让我至今怀念。
《论语》中,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用来形容钱青老师非常合适。没有和老师接触之前,她给我们这些小家伙的印象确实是十分严肃的;但是真正和老师接触之后,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我们所见到的是慈祥的、常常微笑的老师。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刚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就邀请大家去她家中作客茶叙。钱老师就住在北外西院,不大的一套公寓,家具和装修都很简单,但是有一样装饰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客厅的空中悬着几条细线,上面挂满了各色各样的贺年卡,这些贺年卡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们寄来的。这些朴素的祝福给老师带来的快乐,远胜于物质的财富。茶叙时,老师端出一些很精致的外国饼干,配以各种甜咸口味的果酱、奶酪等等。我们多少有些拘谨,老师微笑着对我们说,既然来作客,主人端出的饮食,不吃反而是不礼貌的,大家才放松地吃起来。但在学术上,老师的要求就很严格。我研究生期间第一篇课堂论文写的是沃顿《欢乐之家》,具体的题目,现在自己也不记得,却记得老师的批评:“这个题目没有什么意义。”这真让我悚然而惊,真切地懂得了学术的严谨。另外一次,我在论文里用错一个单词,把时钟的滴答声(tick)错写为敲打发出的响声(click),也被老师一眼看出加以纠正。这样的故事,相信钱老师的每一位学生都能说出很多。
钱青老师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是一位洞明世事而仍然满怀热情的、慈爱的智者和导师。我有幸在学术和人生的起步阶段受到老师的教诲,没齿难忘。老师从容的、慈祥的微笑,帮助我在浮躁的时候沉静,在怠惰的时候警醒,在失落的时候振作。愿老师在不朽的精神家园中安息!(2020.08.18)
文章作者


独芒
发表文章28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96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