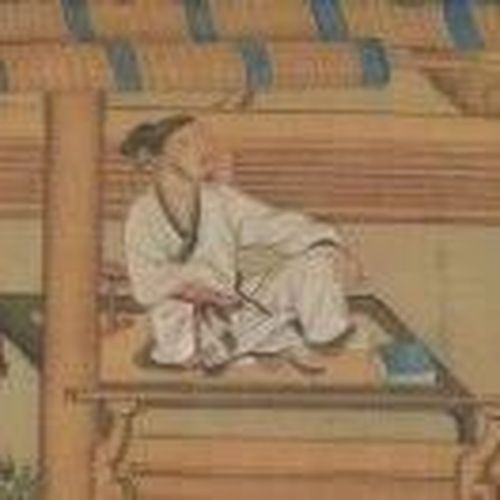到乡村去
作者:贾冬婷
2018-02-07·阅读时长1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318个字,产生7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贵州黎平地扪侗寨一户人家新居盖瓦仪式上,上百村民前来帮忙传递瓦片。这项工程并非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这种仪式感在村民心中似乎更为重要
)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11个推荐 粉丝1344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