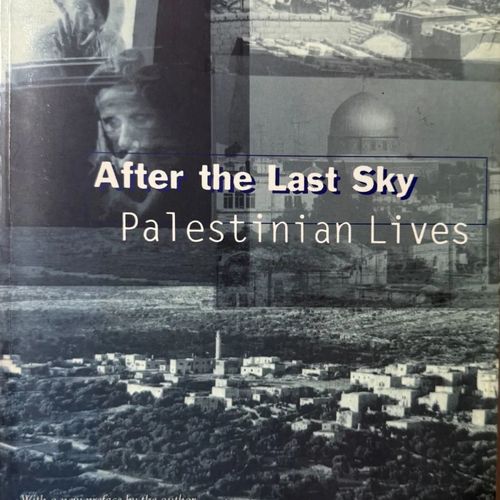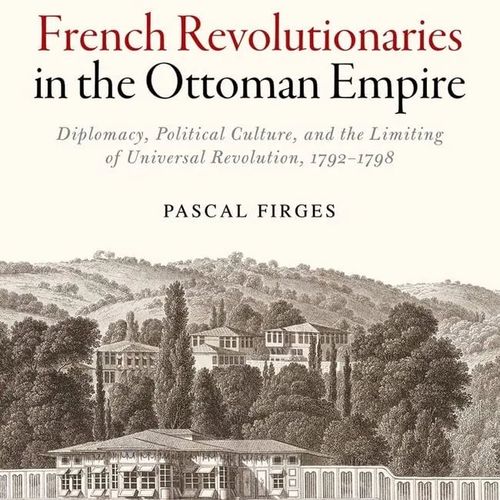香奈儿·米勒的战斗:一点省思
作者:读书
2021-03-24·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541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郦菁
一位性侵受害者决定夺回自己的名字。她叫香奈儿·米勒,有一半华人血统,一半犹太血统。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她在酒后无意识的状态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被在校学生布罗克侵犯。从此开始,在长达四年的司法过程中,她都以埃米莉·多伊的化名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之中。埃米莉时而是一个被动无助且面目模糊不清的受害者,时而是酗酒无度、专擅昏厥的 “派对动物”;甚至被假想成一个放荡的红发女郎,或是拉丁裔女性。化名的初衷当然是保护受害者的隐私,但正如香奈儿自己所言:“我厌倦了作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存在,他们书写我的故事,我却对此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夺回自己的名字,正是为了夺回叙述的权利。这是一场她与媒体、与公众、与性侵犯们、与司法系统,以及与自己的战斗。
起初,难以承受的耻辱和愤怒迫使她把自己一分为二:埃米莉的那部分,可以把所有混乱和痛苦都交给她,然后或是切割掉,或是暂时 “放在一个罐子里封存起来 ”;香奈儿的那部分,则竭尽全力维持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 “垂直分裂 ”。但在此后每一个脆弱的时刻,这种二分法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而香奈儿选择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来解决这场战斗,陈述自己真实的遭遇与怆痛。文学对她不仅仅是疗伤之途,也是找回敏感性与整全性的实践。由此,香奈儿得以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重获对于身体和情绪的控制权。香奈儿最终与埃米莉和解。难能可贵的是,香奈儿从未陷入一种命运无常的怨恨,或者是对伤痛不加节制的书写。感性化从来只能导致认知的关闭,自我的踯躅不前。实际上,她的作品可以打开更多的反思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关心性侵幸存者的心灵状态,或是现代社会中性别关系的一般结构,抑或是个体与制度对抗中的持续困境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次生伤害与“性侵幸存者”
性侵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孤立事件,而是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物,是源自某些不平等和剥削性社会关系的犯罪类型。侵害的发生比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妮弗·赫西与西玛斯·汗教授在二○一四至二○一九年所主持的校园性健康与性侵害调查显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女性曾遭受不同形式的性侵,而男性比率为八分之一,其他非传统性别群体更高达三分之一。同时期其他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至少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性侵诉讼数量居高不下,但定罪率往往是最低的之一,这源自超低的认罪率和超高的撤诉率。戴利与鲍赫斯二○一○年的数据说明,前英联邦国家中只有大约 14%的性侵案例报警,其中 30%进入诉讼环节,其中又只有 20%进入法院审判,而最终的定罪率仅为12.5%。
如此普遍的司法 “正义差距 ”(justice gap),遮蔽了性侵带来的长期而多重的伤害。首先当然是对于个体控制和保护自身身体这种最基本权利的破坏。这并不因性侵结束而结束,恰恰是性侵之后才渗透到自我的每一个角落,如阴影一般跟随受害者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对于身体的使用。所有的羞耻、痛苦、恐惧与焦虑,都是事后才一一接踵而至的。香奈儿在事发当时因为醉酒失去了意识,因两位路过的瑞典学生见义勇为,她才得以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她被告知自己 “成为 ”强奸受害者。但这种表面上的间接性并不能丝毫减轻她的创伤:她的自我碎裂了。在此后数年,她惶惶于每一个脆弱的时刻,害怕突然失去保护,她的精神和身体开始萎缩。
相比之下,另一种次生伤害发生在司法领域和公共空间。对于其人格的质疑和贬损,关于过往性经验、性侵细节的无穷尽拷问,使得受害人一次次陷入 “再创伤化 ”的经历,很多甚至比性侵本身更为剧烈。实际上,根据美国的法律,法庭质询禁止提及原告的性经历。然而,辩护律师可以有一千种替代性的方式来发问,比如:“你有男朋友吗?你专一吗?你性活跃吗?你有劈腿的历史吗?”媒体的审判往往更加缺乏约束。香奈儿在医院接受询问时的陈述是最早被公开的材料,而事实很快被挑选和重构了。在此后的报道中,她参加兄弟会派对,在派对上喝了几杯酒,喝得失去意识等等事实被反复渲染,而另一些细节则被抹除,比如施害者在派对上还试图接近香奈儿的妹妹,并在侵害过程中发照片给好友加以炫耀。香奈儿曾坦言:“我感到我生活的围墙被推倒了,整个世界都爬了进来。”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76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