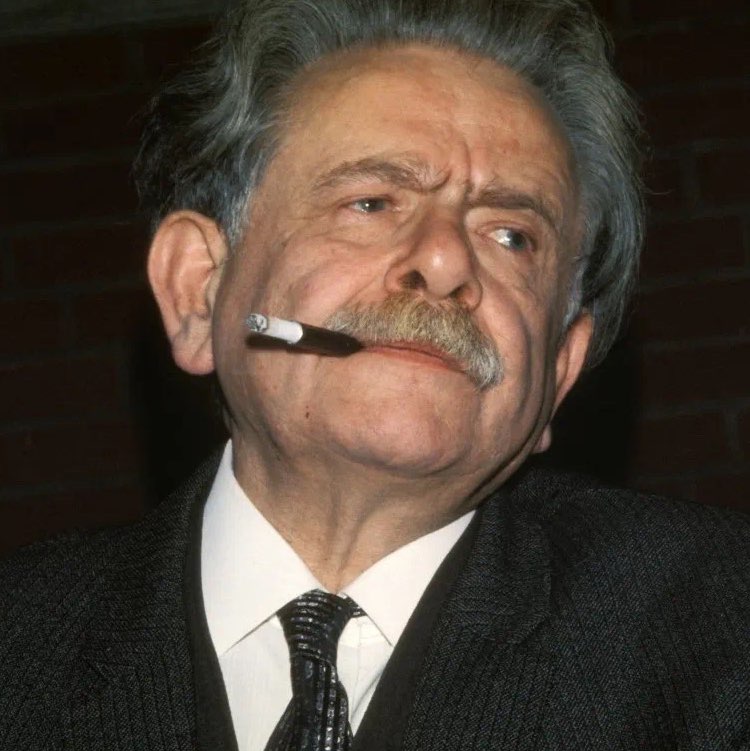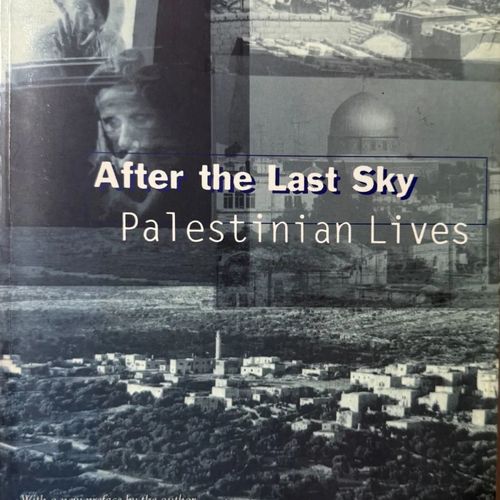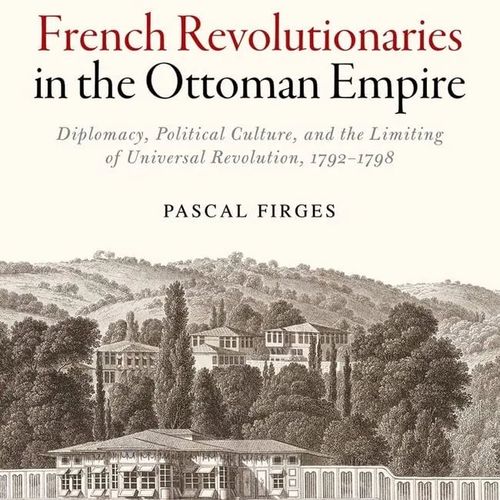无处安顿的女性
作者:读书
2021-03-24·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272个字,产生7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葛耘娜
“男主外女主内 ”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性别角色设定。时至今日,选举平等、同工同酬,女性已然合法地走入公共世界,却仍时刻需要回应这种社会期待。女性依然在努力冲破这个设定,更有甚者,会将所有相关问题上升为性别战争,社会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也随之走向极端,谈“女权 ”而变色。同时,在女性群体内部,“职业女性和全职太太是友是敌 ”的发问,令人对女性是否能够作为整体去寻求处境的改善而深感忧虑。
尽管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上,中西社会差别巨大,但在 “男主外女主内 ”的意识上却不难找到共鸣。事实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爱尔斯坦的《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一书(以下简称《公》)讨论的正是上述困境。
一、公共—私人边界的划定和逾越
“公共——私人 ”这组概念是西方性别研究的一个关键入口,在西方思想源头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二元的世界:公共领域是言说的空间,而私人领域则寂寂无声。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限定在沉默的区域,公共的话语则由男性公民垄断。
在爱尔斯坦看来,柏拉图算是密尔之前对女性最友好的思想家,在他由言辞构建的城邦里,少数优秀女性能够成为护卫者。只是,女性成为护卫者,多大程度是出于护卫者群体再生产的需要呢?或许女性能否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柏拉图构想的前提 ——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分别对应着理性和爱欲,公共世界至高无上,私人世界则对公共世界构成了威胁。因此,理想国实际上建立在对私人生活、私人目标严防死守的基础上,正义秩序的代价是取消私人领域,铲除家庭和婚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公私之间的冲突。
真正把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的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假设在公—私界定中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男性统治、女性服从都是天性使然。女性仅有不完全的理性,因而只能在家庭这个 “必然王国 ”中度过一生。不过,爱尔斯坦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古希腊 “厌女症 ”的批评上,会忽视亚里士多德带来的重要启发:“……什么才是可行的政治、政治共同体以及公民身份 ”(《公》,57页)。这对女性主义或许意味着:要开锁首先需要弄清锁的结构。
爱尔斯坦指出基督教的兴起将一场道德革命引入,带来了公——私界限的松动。其中,语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奥古斯丁是古希腊 “厌女症 ”的破坏者,他用被压迫者的语言发出了声音,因而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也得以打破沉默。随后,路德不仅肯定个体的信仰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共同的生活,还支持教徒使用本地的、普通人世俗的语言去探讨重大问题。女性的日常语言就是方言,这使她们得以跨越过去由特定语言和学识构成的藩篱,改变因为普遍缺乏教育而造成的 “失语 ”。
不过,基督教革命之后,短暂的转机消失了。马基雅维里对德性概念的重塑再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公——私领域划定的界限,同时,他将 “善 /恶”等评判私人德性的语汇踢出了公共领域。由此,不止重新划定了公——私界限,而且扩大了二者之间的裂痕。爱尔斯坦指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可视为对软绵绵的、女里女气的基督教德性的一种防御。”(《公》,106页)不过,新的德性概念与体力及武装的公民相联系,对于身体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公共领域再次变得遥不可及。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5个推荐 粉丝20776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