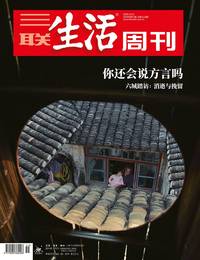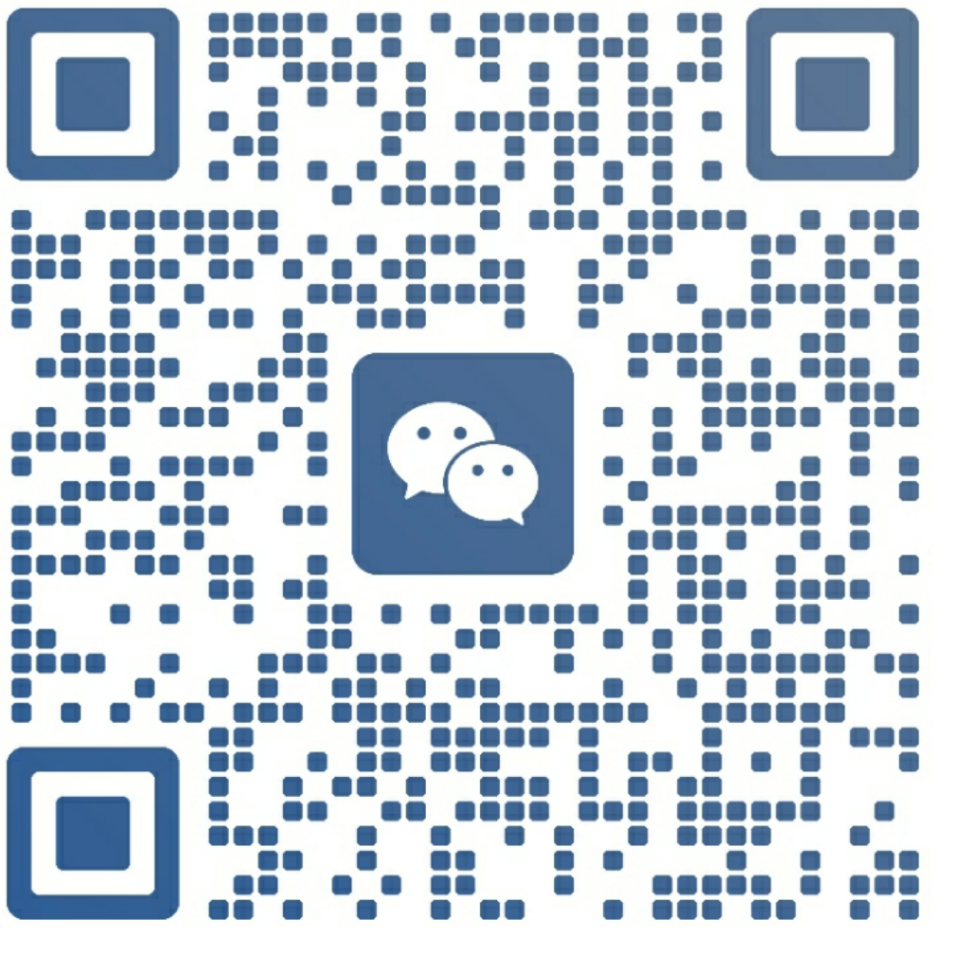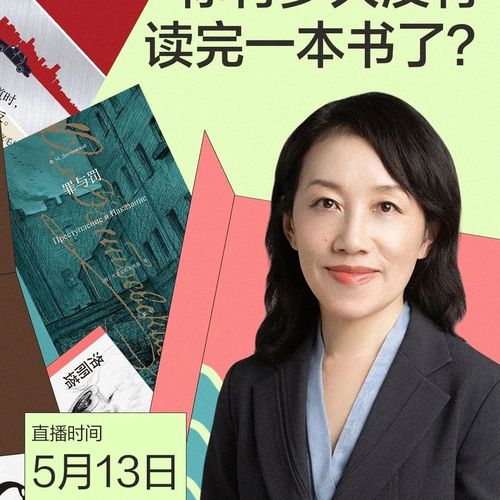上海:12场并非大受欢迎的方言讲座
作者:张星云
2020-12-16·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864个字,产生3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1843 年上海对外开埠后,沪语逐渐成为吴语地区的强势语言
本文摄影/吴皓
特别的讲座
那是2015年10月11日,一个周日下午。上海复旦大学旁的鹿鸣书店,像通常周日那样,将书店中间的移动书架移开,摆上座椅,架上投影仪,等待听众入场。不过这并非鹿鸣书店办过的众多学术讲座中的普通一场,特别之处在于,这场讲座使用的语言是上海话。
刘震回忆说,现场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感。
作为铺垫,早在鹿鸣书店几天前在微信公众号贴出的海报上,除了发布主讲人——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的身份,以及讲座题目《叙事与图像——欧洲和印度艺术的情节展现》之外,海报上还特意标明了讲座使用的语言——沪语。
令刘震意想不到的是,来的30多位观众里,绝大部分是中青年。讲座很热闹,从开始到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所有人都默认用沪语讲话,一些观众只能听懂但张不了口,另一些观众,则是只要张口就会用带尖团音的老上海话,但没有一个人问过他“为什么要用沪语讲座”,就好像大家都明白他的用心。
讲座中刘震侃侃而谈,从他翻译的德国著名印度学家迪特·施林洛甫作品《叙事与图像》讲起,介绍西方对艺术中故事情节布局的关注,以及用文献学的方法,分析古希腊神话、《圣经》和佛教故事在不同文本和图像中的变异,当然,所有这些,刘震都是用上海话,也就是沪语讲的。

上海成为国际性的移民城市后,沪语与各地方言融合

现在上海年轻人最多只会说沪语发音的普通话
这席演讲,刘震只是将原来在学校上课时的一个讲座内容搬过来,没有为转换成沪语做任何特别准备,遇到人名地名,也不用普通话音译,而是选择用原文或者英文。“没打过腹稿,就直接讲了,讲完就觉得特别爽。”刘震描述那种感觉,“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用沪语讲与上海无关的东西。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如此自如地驾驭一种语言,那种直接从脑子里蹦出来,只有母语才有的亲切感。”刘震说后来系列讲座的其他讲者也都是差不多的感受,觉得讲完哪怕不要报酬也很爽。
当时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作为中心主任,刘震手头有一些活动经费,于是与鹿鸣书店老板合计,办了“印度学与印度研究系列讲座”,刘震的初衷是,让每一个人都使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进行学术交流,方言不仅用来说俚语或者鸡毛蒜皮的小事,完全可以用于严肃场合的学术讲座,讲正经题目。
于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离休领导用沪语讲了一场佛教与摩尼教文化交流的讲座,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一位美籍华人,用母语沪语讲从悬泉置汉简看早期丝绸之路。讲座越走越远,刘震的一位同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同样来自上海的美籍华人,分别用沪语和藏语各讲了一场印度诗学的讲座,第二场讲座就来了很多藏族听众。
也并不是每场讲座都顺利。复旦大学佛教研究团队负责人,一位著名佛教哲学家,祖籍广东,他决定用粤语讲从克莱因的《知识与解脱》论国际上的内亚佛教哲学研究,结果讲到一半,被底下的观众要求换成普通话讲。
刘震说,在这个系列讲座里,演讲人最需要的特质是勇气。“语言学里有个概念,叫‘lingua franca’,即地区性权威方言,其实沪语和粤语都算是这种强势方言了。强势语言的特点就是,你一开口,人家不会笑你。但当你的母语方言被沦为‘土话’时,你在大雅之堂用方言讲话,一开口,就会被人嘲笑。”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位老师,就在刘震的系列讲座里用无锡话讲《摩诃僧祇律》中的环保思想与文学故事,在沪语尚且式微的上海,无锡话更加不属于强势语言,而那位老师,也非常有勇气。刘震还曾邀请过同行前辈来做沪语讲座,“平时交流都用沪语,但他受到邀请后,坚持要用普通话做讲座”。
这样的讲座,刘震一共组织了12场,横跨一年时间。但后来观众越来越少,有次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用沪语讲丝绸之路上的通货,现场算上刘震,只来了三个人,“即便这样他讲得也很爽”。有关印度的话题,全上海能请来讲的学者都请了一圈,讲者们也渐渐失去了新鲜感,此时,活动经费又收紧了,讲座无疾而终。
再后来,曾经讲座中认识的一位热心观众,为刘震联系到了虹口图书馆,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形式,刘震在虹口图书馆又讲了一遍,“但效果不好”。
文章作者


张星云
发表文章193篇 获得11个推荐 粉丝1031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