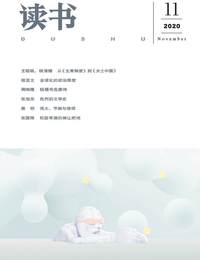跨境地图:一个全球史的故事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008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于京东
二○一五年求学巴黎期间,笔者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图部看过一幅图,这是荷兰制图师弗雷德里克·德·威特(Frederick de Wit)出版于一六八九年的《鞑靼、蒙古、日本与中国新地图》(1689, BNF, Cartes et plans, GE D-16737)。其中,在长城以北的尼布楚城(Nipcheu)一带,作者用拉丁文标示了一段文字,内容是:“一六八九年,法国的耶稣会士 Gerbillon(张诚)被中国皇帝派到这个城市,与莫斯科协商和平方案。”
在资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幅地图堪称一次外交史上的 “消息速递 ”。一六八九年六月,清朝面对内忧外患,康熙皇帝决定同侵犯边境的俄国订立和约,同时派身在北京的两位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和法国人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全程协助,形成了中、俄、耶稣会这个 “奇异的三方组合 ”(Joseph Sebes)。八月,谈判的各方抵达尼布楚。九月,和约达成,依国际法规则签署、盖印、换文和宣誓。这一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为欧洲所知悉,并辗转记述于荷兰人的这幅大地图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外交流与知识旅行的一个缩影。
尼布楚的两幅地图
这个故事可以先从亚洲讲起。一六八九年,在中俄两国的谈判桌上,双方各自拿出了一幅地图。清廷钦差手持《吉林九河图》,而俄国人则使用《鞑靼北部与东部图》(1687,BNF, Cartes et plans, CPL GE DD-2987-7372B),后者是另一位荷兰制图师尼古拉斯·魏特森(Nicolaas Witsen)的作品。同德·威特的一样,地图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赤道平面投影,标有经纬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地区的空间轮廓与地理知识。中方的地图同样试图描绘这片区域,但使用的是传统舆图的制作技艺,既没有投影法,也不画经纬线。因而,尽管两幅地图上都标识了重要地点,山脉河流的方位也大致吻合,但制图术的差别造成了领土表象上迥然不同。对此,在场协助谈判的两位耶稣会士都在日记当中有所记载。
在耶稣会士看来,来自北京的官员尽管手持地图,却对图像与疆域之间的实际对应缺乏认知。故而,“诺兹山脉 ”(今外兴安岭)一带看似只有 “毫厘 ”,在俄国人的大地图上却差之 “千里 ”,引发的争议一度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徐日升将此解读为清廷官员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交经验的匮乏,而同行的张诚却将注意力放到两幅图的技术差异上,并且打算另绘制一幅新地图作为礼物献给康熙皇帝。事实上,从尼布楚回京后不出数月,张诚便呈送了这幅新的亚洲地图。此图依照西式制图法,标有地理数据,但并不完整,因为图上的中国北方地区标绘粗陋,存在大片空白与模糊地带。
以地图作礼,并非法国人首创。十七世纪初,利玛窦在面见明朝的万历皇帝时,也进献过一幅《坤舆万国全图》。为讨欢心,利氏还稍作改动,将 180°经线放于此图中部,中华帝国由此也就处于世界的中央。相较于前辈这件赫赫有名的献礼,一六九○年张诚的地图后人鲜有问津,对当时地理空间的绘制也算不上完整。但当康熙手持此图,御览疆土时,国土空间的已知与未知跃然纸上。其时正值内忧外患,常听耶稣会士讲学、青睐西洋科技的皇帝对法国人的制图技法刮目相看。适逢京城附近的白河决堤,需要舆图配合治理,一七○五年,他决定让法国耶稣会士来测绘一幅地图,这正中张诚等人的下怀。
一六八五年三月,张诚、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李明(Louis-Daniel Lecomte)、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在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启程时,王室是委托了制图任务的。他们被授予 “国王数学家 ”(Mathématiciens du roi)的称号,个个精通数理几何,擅于测绘。临行前,国务大臣还专门会见了他们,由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亲自制订了用于测量经纬度的表格,还配备了最新的科学仪器。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派遣这个使团并非纯粹为了传教事业,同行的居伊·塔夏尔(Guy Tachard)就说:“国王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致力于发展科学与艺术,所以特地派遣我们前往海外观测,进而修正地图,发展航海和天文事业。”所以,搜集亚洲内陆数据,绘制中国新地图,是耶稣会的另一项重要使命。但此事到这里也只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故事发生在欧洲。
地图业的“中国热”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与海外事业的拓展带来了一股“地图热 ”,它源于一种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基调和征服自然及世界的普遍主义信心。这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系列的空间探索与制图活动,不仅带来了知识媒介与视觉技术的革新,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总体性的观念、意识与秩序,施密特(Carl Schmitt)谓之 “空间革命 ”。它在欧洲促成了有精确边界、中央集权与普遍理性的主权国家的诞生,其典型就是法国。在海外,全球互通伴随着传教事业的推进与来自新世界的地理、信息、知识反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地便是中国。
恰逢此时,巴黎成为欧洲制图行业的中心。沿着塞纳河右岸卢浮宫画廊(galleries du Louvre)一侧往上走,河中心的西岱岛(l’.le de la Cité)和巴黎大学所在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聚集着大量的地图出版商,包括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菲利普·布歇(Philippe Buache),等等。这些地图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王室的教师 —“国王地理学家 ”(Géographe du roi),也是当时巴黎的著名商人,通过特许和专营制度来生产、销售地图。除了宫廷和贵族的资助外,社会大众也喜好购买和阅读新地图,这进一步促成了地图的产业化,市面上的一幅地图要先后经过测绘、刻版、印刷、上色、售卖等各项环节,商人们因此获利不菲。
中国地图一度是紧俏产品。在耶稣会促成中西文明交流后,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古老东方的浪漫幻想与知识渴求。宫廷内部流行着 “中国风 ”(Chinoiserie)的器物、装饰与艺术,公共领域也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 , 1755)所痴迷,这同 “文明与世界 ”的时代话题紧密结合。一时间,对中国文化与地理知识的需求成为一种普遍热忱。然而,一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段,市面上的中国地图却相对短缺,已有的产品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主流产品大致有两类:一是以传统中国典籍和舆图为底本,经耶稣会士带回后,由专业制图师重新编绘的。一六五六年桑松的《中华王国地图》( 1656, BNF, Cartes et plans, GE SH 18 PF 224 DIV 4 P 7 D)就是出自马泰尔·内罗尼(Matteo Neroni)一五九○年的原本,后者依
据的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带回的材料。二是基于航海与商贸记录,侧重描绘沿海地区的地图。如一六七七年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Val)所出版的《中国地图》(1677, BNF, Cartes et plans, CPL GE DD-2987-7171)便是根据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出使中国的记述所绘制,后者在一六五五至一六五七年曾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
使团从广州航行到北京。
两类地图都无法提供完整中国的地理图景,不仅对内陆和北方地区描绘粗疏,而且缺少统一的测绘标准。所以,除了国王使命,十七世纪末的法国耶稣会又多了一个动机去绘制中国地图,并且试图用新技术来淘汰市面上的传统作品。然而,要实现这一宏愿,他们还面临着三个主要对手。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72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