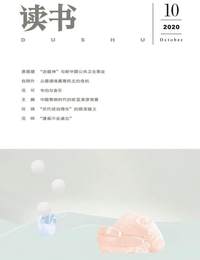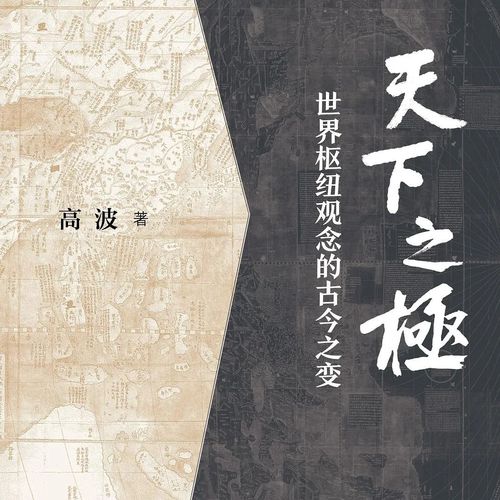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作者:读书
2020-10-21·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874个字,产生1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易莲媛
一九五三年五月,偏远闭塞的江西余江乡下来了一批专注 “污秽之事 ”的怪异陌生人。他们据说是来解决困扰当地已久的 “大肚子病 ”,但却总是在逐户征集粪便样本,提各种让人羞于回答的问题,打听如厕和处理排泄物的方式,还用科学仪器仔细观察这些本不应见人的东西。为避免尴尬,也为了不给农忙增加负担,群众甚至干部纷纷借口 “没空”避开了。的确,这里没有固定厕所,农民们白天下田劳动,就地解决,随身携带样本盒相当不便;晚上全家人共用一个马桶,也很难为每个成员分别取样。而且,习俗上都是由家里地位最低的儿媳承担清洁马桶的工作,对这些年轻妇女来说,无论是单独处理异性长辈的排泄物,还是把自己的样本拿给外来同龄人检查,都足够难堪。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并不明白治病与粪便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即使后来承受了上级压力,群众也不愿严格按要求取样,很多人或者直接交出空的样本盒,或者用小孩子的样本冒充,甚至以泥土、牲畜粪便等其他脏东西伪造。他们抱怨道:“这不是来看病的,是来查我们生活水平的 ”,“我没东西吃怎么拉得出来 ”。
以上场景,被记录在高敏(Miriam Gross)的著作《送瘟神:毛主席的消灭寄生虫运动》(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2016)中,描述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项大型传染病防治运动正式开始前的调研所遭遇的挫折。而随后展开的,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卫生运动之一,“血吸虫病防治运动 ”。
高敏的研究直接以血防运动为对象,以此前研究很少关注的地方档案为基础,聚焦上海市区、上海郊区青浦(一九五八年前为江苏青浦县)及江西余江三地。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发现相对这一运动在其后二三十年所经历的技术、资金、人力和组织挑战,前文提及的群众对早期摸排工作的不配合仅仅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不过,也正是从这些困境及对它们的克服出发,高敏在 “二战 ”后亚非拉地区抗击寄生虫病历史的比较视野下,就“血防 ”工作的具体进程、各项措施的有效性和最终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都提出了与通行观点不同的见解,并由此出发重估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经验,进而探讨在有限的技术与资本条件下如何协调公共卫生体系中专业化人才、知识与基层社会的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
受一九五八年《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影响,远离疫区的人会以为血吸虫病在五十年代末已基本消灭。事实上,当时只有试点之一的江西余江县控制住了这种疾病,全国层面的胜利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最终到来。成功的关键,以往一般被归纳为 “预防为主 ”方针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卫生运动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在研究了大量的地方档案,特别是合作社、生产队等基层工作报告与备忘录后,高敏指出,在实现 “血防 ”目标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非预防,而是对已有感染者的治疗。一开始的各项预防措施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甚至其中某些不够科学的做法还导致了六十年代初血吸虫病在部分已经得到控制的地区卷土重来。至于另一个关键要素农村合作医疗,高敏比以往的研究更强调其基础性、根本性作用,但她对这一制度核心的理解并不同于主流框架。据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九七八年在《阿拉木图宣言》中的说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经验是以大众健康教育推动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地方创新,培养非专业化的 “赤脚医生 ”提供廉价基础医疗服务,集中力量于低技术含量的预防活动而不是昂贵的治疗。但高敏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在 “血防 ”上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持续投入,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患者不再需要承担治疗费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专业人才与技术知识长时段内从城市向农村的扩散,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下放农村的专业医护、技术专家广泛参与到基层病患的治疗与赤脚医生的培养中来。换句话说,专业技术、人才在政府主导下的再分配和财政上的倾斜,而非向现状妥协的低技术策略本身,才是农村合作医疗的核心与 “血防 ”成功的关键。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8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