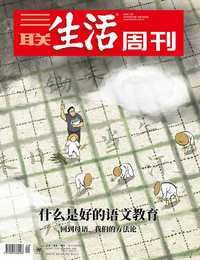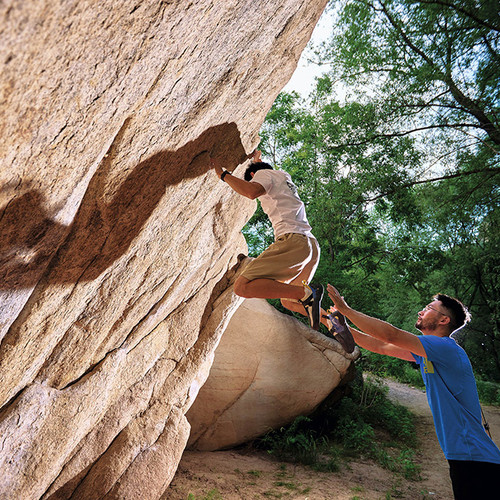文学如果没有和内心的关联,它有什么用?
作者:孙若茜
2020-07-15·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139个字,产生24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张悦然(黄宇 摄)
口述/张悦然
采访/孙若茜
我的作文很难达到应试的标准,而且还容易写不完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我读的是山东大学的附属小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学校设施很简陋,老师基本都是大学老师的家属,来我们学校解决工作问题,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大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男老师。其他女老师都在办公室讨论猪肉价格,交流如何织毛衣,只有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书,显得格格不入,特别孤独。刚来那年冬天他又摔断了胳膊,右手一直挂在胸前,有时候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们就会看见他用左手吃着方便面。放学的时候,又看他身披一件驼色风衣,用左手驾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骑走。总之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悲情的角色。
我们每周有两节作文课在周四下午连着上,每次上课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个故事,然后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想法把它重新写下来,你可以发展原来的故事,也可以改写它。那些动人的故事我从来没听过,和语文课上学的其他东西完全不一样。他这个方法激起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渴望,通过用自己的话重述故事,我们得以将它们据为己有。我特别希望他觉得我写得好,这是我在整个小学阶段最在意的一件事,他一定也知道我在意他的肯定,他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个女生每次听故事时专注甚至近乎于紧张的神情。他也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个女生花了比别人都多的时间去写故事,作文本总是很快用到最后一页。但他从没给过我最高的分数。也许是因为我的野心太大,通常用力过度,因为太想把那些故事变成自己的,我总是背叛原来故事的意志,生造出新的情节,从而把它引向别的方向,最终变成另外一个故事。而新的故事远不如原来的那个好,当然我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后来我才知道,他讲的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比如《二十年后》《最后一片树叶》。欧·亨利的小说的转折性结尾,本身具有很大的能量,是很难篡改的。也许这位语文老师想要做的事,正是让我们在徒劳的画蛇添足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作品所具备的完整和统一性,让我们感受到其中所体现的“叙事的权威”。那一年的作文课对我的影响很大。
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得过奖,但是上中学之后分数一直不算很高。好像在刚开始写作文的年龄段,老师都愿意从你的文章里挑出一些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就像现在看网上流传一个9岁小朋友的作文,我们会在里面看到没有被驯化的东西,会觉得他的想法有趣,应该鼓励。但是中学作文的批改标准并不会在意这些,而是慢慢变得模式化了。我的作文很难达到应试的标准,而且还容易写不完。可能是因为作家不太会长话短说,思维总是发散的,越写越长。考试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赶快收尾,而不是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框架。所以虎头蛇尾是我的那些作文最大的问题。作文事实上考察的是如何使用有限的时间来把自己想讲的事讲清楚的问题。写作文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时间是别人给你的,像借来的筹码。但是对作家来说,即便是创作时间再不自由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也会拥有一种自己掌握着时间,时间站在他这一边的尊贵体验。
那时我还很害怕考试题目是议论文,因为它们很容易暴露我缺乏见地、幼稚简陋的思想。议论文要求你对命题人提出的事情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好像这很自然,你应该对任何事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事实上,我的确对很多事没有看法,也缺乏探讨的热情。不过你依然可以提前准备一些“想法”去应对这种题目,那些想法大多看起来很新,但其实非常保守,符合某种政治正确。
我是在中学时代发表第一篇小说的,小说的名字叫《诺言角落》,写的是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我爸爸的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偶然读了它,觉得我写得很好,就拿到了一个并不适合发表小说的学术杂志上。那件事对我影响不是很大,当时对我来说最开心的还是能表达,而不是需要得到回应,因为很多时候是连表达的时间和空间都没有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要交日记,我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在日记上连载起了故事,老师显然不是我的理性读者,她只是淡淡地写下一句评语: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的故事后来没有写完,但我想老师并不介意这一点,虽然我在心里设计了一个动人的场景:当我们在走廊擦肩而过的时候,她忽然问我,后来呢?那个故事后来发生了什么?
文章作者


孙若茜
发表文章103篇 获得25个推荐 粉丝709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