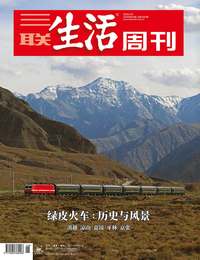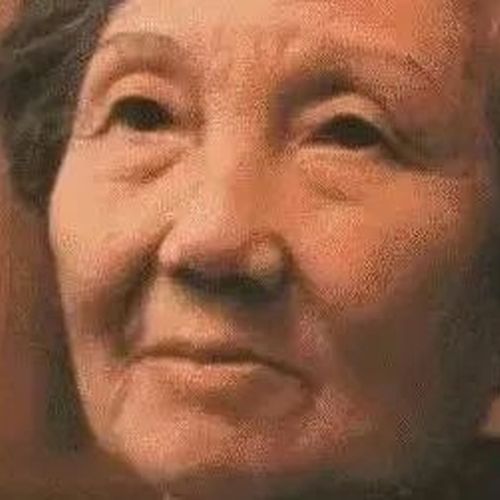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作者:李菁
2020-06-24·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210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巫鸿(黄宇 摄)
西方的中国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哈佛读的是人类学,导师张光直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弟子——李济先生当年在哈佛学的人类学,也是第一位拿到人类学博士的中国人,后来从事了考古。有意思的是,你的人类学的背景,与后面所从事的艺术史研究也不是一个范畴的。现在回过头看,人类学的专业背景对艺术史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巫鸿: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是比较深层的影响。我在哈佛的第一年主要学习人类学。其实我当时在国内申请时,对于到国外学中国美术史并不特别理解——干吗去国外学文物和艺术?当时觉得应该学一些国内没有的,特别是人类学——当时中国只有社会学而没有人类学,所以一听到还有一个研究“人”的学问就感到很受吸引。
到了哈佛之后,我发现美国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性特别强,而且研究对象主要以美洲为主或类似的东西,和我的兴趣联系不太大。但是它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以“人”为中心。一直到现在,我做了很多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包括当代艺术的研究和策展,我都是把“人”作为中心,而不是把器物或者作品作为中心——或是关于艺术家,或是关于武梁祠那种艺术品背后的赞助人,都是“人”在起作用,这可能和我的人类学背景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艺术都是人的创造、人的表达,它的变化很多也是和人的社会、人的宗教、人的思想、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只从作品到作品或者从形式到形式,完全从艺术风格的发展谈作品,一个是感觉比较隔阂,一个也比较枯燥——脱离了“人”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式或技术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后来离开哈佛大学,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你的东方背景会对中国的艺术形式和中国文化更了解,是否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或者想法,付之在对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的建立的实践上?
巫鸿:我虽然在国内原来学的是美术史,但是当时的美术史系刚刚起步,而且在“文革”中就停了,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中国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强的中国美术史体系。因此并不存在“我以一套中国的美术史观念去和西方抗衡”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种虚构的对抗。
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说的“西方”实际上是“现代”,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将之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国情结合。我这一代已经很难说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们不是背古文写毛笔字长大的、是一种现代型的中国人。当然中国文化的根基肯定是存在的,特别是语言和文字,这是和西方学者最大的不同。应该承认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和古代文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城市里长大,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也要通过发掘和研究。
我去芝大肯定是想做一些新的事情,但不是把“西方”做靶子去反对,而是根据我对美术史的理解去发展国际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学者”往往是比较个人性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代表什么。所以当有一位西方学者把我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写文章批评我,我就说我怎么能代表中国学者?我从来不代表谁也不能代表谁,他那么认为是他的看法,我们不能跟着采用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我觉得我的写作和教学是从我自己的教育和经验,包括在故宫、哈佛以及别的地方得来的,是一种个人化的经验过程。
文章作者


李菁
发表文章206篇 获得14个推荐 粉丝11209人
文字工作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