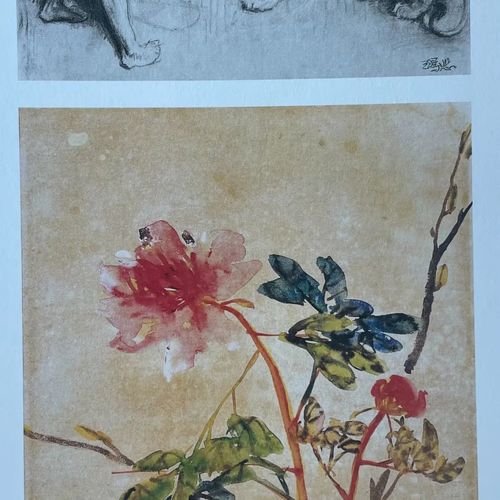爱是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现象
作者:读书
2019-11-13·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662个字,产生6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曹卫东
一
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精神,按照洛维特著名的说法,由歌德和黑格尔携手发端。在其《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洛维特开门见山地写道:“歌德使德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而黑格尔则使德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故此,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精神往往又被称为“浮士德精神”,足见歌德开时代之先声的伟力。《浮士德》气势磅礴,并非一部好读好懂的书,那它究竟讲的是什么,才能赢得如此赞誉?—“一八○六年,当拿破仑经过耶拿和魏玛到来的时候,黑格尔完成了《精神现象学》,歌德完成了《浮士德》的第一部分。在这两部著作中,德国语言达到了其最广博的丰满和最深刻的精炼。”
正是与《精神现象学》的对照,使我们能一窥歌德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史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标志着人类精神最高理想的实现。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必须通过成长才能达到其制高点。作为个体的拿破仑,不过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成长与共同体成长具有了同构性。歌德以诗剧《浮士德》来把握个体的成长史,黑格尔则以《精神现象学》的哲学论述来把握人类的成长史。两者既有体裁之别,又存在着思想质地的差异。总体上看,《浮士德》由五大悲剧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分为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对于知识悲剧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寓意。浮士德从枯朽的知识沉积中,通过与魔鬼的赌约,走向生命的历练。这是浮士德精神世界的最初发端。而浮士德与甘泪卿之间的爱情悲剧,虽然占据着《浮士德》第一部分很大篇幅,但通常仅被视为文学史上的佳咏。除了激赏它的文学价值之外,其中蕴藏着的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挖掘。
按照歌德的理解,人要成长,必须经历知识追求、爱情生活、政治生涯、艺术追求、事业追求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恰好对应《浮士德》中的五大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以及事业悲剧。人的成人之路,必然伴随着这些悲剧的历练,从一个阶段迈入下一个阶段,直至完成生命周期。实际上,爱情悲剧并非可有可无的经历,反而是这五大悲剧的核心所在。走出书斋的浮士德,正是经由爱情,初次遭遇了“共在”问题,方始介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对爱的描写,并非《浮士德》中恣意挥洒的闲笔,而恰恰是人类精神成长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
爱的现象向来为歌德所重视,而从创作角度来说,《浮士德》中爱的咏叹顺理成章。相比之下,《精神现象学》关于自我意识的章节中,爱的概念却隐匿了踪影。这一章恰恰是整部《精神现象学》的难点,也是后世诸多思潮的思想阵地,历来注家众多,各说纷纭。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实际上对爱的概念十分倾心,一度将爱作为其理论的落脚点,初创了所谓“爱的泛神论”(Pantheismus der Liebe)。因为爱作为主体间的关系,能够有效地弥合主客体的分裂。爱是主体间的一种承认关系。但随着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到《精神现象学》时期,他却放弃了用爱的概念来刻画承认关系。
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专门释义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他尤其关注黑格尔思想的历史发展,将《精神现象学》有关自我意识
的章节视为历史性回溯的出发点。霍耐特从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着眼,认为在黑格尔结束耶拿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霍耐特强调,《精神现象学》把自我意识发展的独特功能派给了为承认而斗争,而这个位置曾经属于那种贯穿在每一个阶段驱动精神过程的道德力量。就“主奴辩证法中”的这一意义而言,主体间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与劳动中的实践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的特殊逻辑几乎完全从视野中消逝了,黑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型。
因此,《精神现象学》之前的黑格尔作品中所展示的诸种承认模式,就被自我意识的辩证逻辑完全掩盖了。霍耐特认为,发展一门批判性社会理论的独特资源,应该到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手稿中(主要指《伦理体系》及《实在哲学》)去寻找。霍耐特根据“为承认而斗争”观念进行了回溯性的重建,指出承认关系具有三种基本模式:爱、法律、团结,其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豪三种未被扭曲的自我关系,而这三种基本模式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首先,爱的关系是最原初的相互承认关系,处理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问题。这种关系涉及主体形成自身同一性的问题。主体在获得了被爱的经验之后,才会首次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具有需要和欲望的主体。不过,当爱从个体之间扩大到家庭层面时,就会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个体之间基于爱的承认关系便会土崩瓦解,需要寻找更普遍化的交往规范。
其次,在青年黑格尔看来,爱是一种情感和依恋,在面对更复杂层面的交往,例如家庭成员在互爱关系中的冲突时,会逐步让位于更高阶段的承认关系。这就是法律的承认关系。此时,人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恋人”的身份转变为“法人”。恋人之间的承认,属于自然冲动的特殊产物,不具有理性的认知。法人之间的承认,则依赖于社会契约,具有理性认知的内涵。一旦建立起法人之间的承认关系,人们在其中获得的更多是尊严感。法律作为社会层面上的承认关系,处理的是人与群体的关系。
再次,霍耐特指出,最高的主体间性关系应为“团结”,是爱与法律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在黑格尔看来,团结就是在它之前的两种承认方式的综合,因为它与“法律”共有的是普遍平等相待的认知观点,与“爱情”共有的是情感依恋和关怀。一直到提出一种关于团结的实体论概念,黑格尔总是把“伦理”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爱情在法律的认知印象中变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普遍团结时,就会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立场中,由于每一个主体都会承认他者的个体特殊性,因此,最高级的相互承认形式也就在其中获得了实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到了第三个承认阶段,主体的身份已然转变为了公民,而承认的问题则扩大到了整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认公民便获得了自豪感,以此实现了共同体的整合。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5个推荐 粉丝20748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