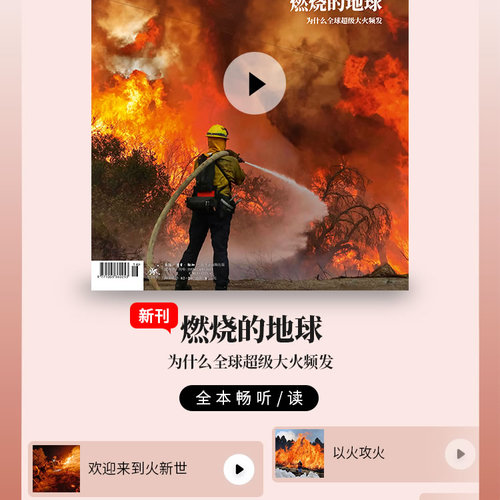以火攻火
作者:袁越
04-15·阅读时长27分钟

计划火烧
“红队向南,蓝队向北,让我们开始行动吧,祝大家烧得愉快!”随着指挥官帕特里克·奥尼尔(Patrick O’Neal)一声令下,一群身穿黄色防火服、头戴各色头盔的消防员点燃了手里的滴火枪(drip torch),草原上立刻扬起了阵阵浓烟。
这是位于美国堪萨斯州东部的孔扎草原(Konza Prairie),大部分土地属于丘陵地,上面长满了枯黄的长草,但在沟壑之间却能看到一丛丛绿色的松柏和灌木,从外观上看像极了东非的稀树草原。奥尼尔是孔扎草原生物学研究站(Konza Prairie Biological Station)计划火烧项目的负责人,手下管理着一支由十几名志愿者组成的火烧小分队。那天正巧是3月12日国际植树节,这支小分队的任务却是通过放火烧荒来清除草原上的松柏和灌木,这让我感觉有点滑稽。
“如果我们不烧的话,这些北美圆柏(east red cedar)就会迅速扩张,很快就会占领整个草原。”小分队里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的志愿者指着不远处的一丛墨绿色的柏树对我说,“这些圆柏的叶子富含油脂,很容易被点燃,而且火势会非常迅猛。前几年堪萨斯曾经爆发过一场超级大火,罪魁祸首就是这些圆柏。”
布莱尔是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K-State)生物系教授,研究方向就是野火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出发前他领着我参观了由他管理的一块小型生态试验场,整块场地被分隔成十几个20米见方的地块,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火烧模式。其中一个地块上长满了圆柏,密密麻麻的叶片把整块地遮盖得严严实实,导致林下几乎寸草不生。紧挨着的一个地块却是光秃秃的,地表铺着一层黑炭,显然不久前刚刚被烧过。不过仔细看就能看到无数浅绿色的嫩芽从黑土里钻了出来,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对照实验,黑色的那块地每年春天烧一次,所以一直保持着草地的状态。另一块地禁火30年,上面的圆柏已经长到五米多高了。”布莱尔对我说,“圆柏是一种产自美国东部的树种,非常怕火,遇火就着,而且一烧就死,所以一直难以离开湿润的美东地区。但因为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的野火越来越少,所以这种树开始了大规模西迁,如今已经成为美国中部地区的主流树种了。业内都称这种圆柏为‘绿色冰川’(Green Glacier),意思是说这种树会像冰川那样逐渐侵蚀所有的土地。”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圆柏把孔扎草原变成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库,每年春天这里都会放火烧荒。但这种计划火烧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进行的,而是对天气状况有着严格的要求。据奥尼尔介绍,影响计划火烧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风,最适宜的风速在每小时5~15英里之间(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因为风速太低的话火不容易扩散,影响工作效率,风速太高则容易失控,烧到了不该烧的地方。除此之外,空气湿度也得在20%~60%之间,道理是相似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野火产生的浓烟不会吹到居民区或者高速公路上。”奥尼尔补充道,“比如我们今天计划烧掉的那块地位于孔扎草原的东侧,紧挨着177号高速公路,草原的北侧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所在的城市曼哈顿(Manhattan),为了不让烟雾吹向东面和北面,我们只有在刮东北风时才能烧。”
从奥尼尔的介绍可以看出,计划火烧的天气窗口是非常狭窄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此前我曾经试图联系南加州的森林管理部门,希望能参加那里的计划火烧,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答复说,南加州不适合计划火烧,一来那里的居民区密度太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天气窗口。二来南加州的灌木太容易着火了,而且火势相当难以控制,一旦烧过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所以南加州依然会采取严禁山火的政策,只能通过人工剪枝和建设防火隔离带等措施来预防超级大火。
无奈之下,我几周前开始联系孔扎草原生物学研究站,但天气一直不合适,直到植树节的前两天气象预报终于确定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窗口期,于是我立刻飞了过来,这才终于赶上了这次计划火烧。
上午11点烧荒行动正式开始,奥尼尔把小分队带到研究站内的一条土路上,这条路是今天计划火烧地块的最西端,处于下风口。十几名志愿者被分成了红蓝两队,分别沿着这条土路向北向南行进。每支队伍由5~6人组成,其中3~4人负责烧,也就是用滴火枪在草地上画出一条火线,然后这道火线便会借助风势迅速向下风口蔓延。另外两人负责灭火,其中一人手拿喷水枪,迅速把烧过的草地浇湿,作为此次计划火烧的终点线。另外一人开着一辆储水车跟在后面,车里装着十几吨消防用水,出水口连着一台高压泵,负责提供喷水的动力。

这块地已经有两年没烧过了,荒草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高,非常容易着火,但火势却并不算大,很快就会因为燃料烧尽而熄灭,所以消防员们很快就沿着这条土路烧出了一条10米多宽的黑色防火带。作为一名新手志愿者,我的任务就是和一位名叫肯·斯塔福德(Ken Stafford)的资深志愿者组成一个善后小组,负责清理红蓝两队漏掉的暗火火点,保证野火不会在我们离开之后再次爆发,于是我俩驾驶着一辆小型四轮驱动工程车在红蓝两队之间来回穿梭,用车上配备的一台小功率喷水枪把火点浇灭。
“现在是整个计划火烧行动里最无聊的阶段,等到两支队伍在上风口会合时就好看了。”斯塔福德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情况,“这块地去年夏天曾经是牲畜的牧场,留下了很多牛粪,这就是暗火火点的来源。”
斯塔福德今年76岁,是一位经济学的荣休教授,退休前曾经担任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K-State)的副校长。他年轻时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从小就喜欢在山里徒步,退休后决定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这个计划火烧团队,一方面能够满足自己亲近大自然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能发挥点余热。
斯塔福德是个健谈的人,我俩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倒也不觉得无聊。这位老校长真的特别喜欢火,只要看到前方出现大一点的火苗就会兴奋地指给我看,而且我发现其他几位志愿者也有这种倾向。我后来得知,团队里的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学生或者退休教师,其中有几位学生的专业就是生态学,自然愿意亲自参与火烧行动。另外几位退休教授则大都是像斯塔福德这样的人,原来的专业和火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行为只能用恋火情结来解释了。

说起来,我曾经也是一个很喜欢玩火的人。上中学时经常和几个好朋友去北京西郊的山里野炊,其实就是带个铝锅煮点方便面什么的,主要的乐趣不是吃,而是玩火。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有句台词深得我心,大意是说他记忆中的北京总有一股烧荒草的味道。这股味道也是我对儿时北京的记忆,不过后来防火成了各级部门的工作重点,西郊风景区的道路两旁经常能见到诸如“山火烧得旺,牢里睡得香”这样的标语,那股烧荒草的味道便再也闻不到了。没想到多年之后我却在堪萨斯草原上再次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虽然仍然很好闻,但似乎有点过于浓烈了。事后想来,应该是和这片草地上有太多的牛粪有关。
下午的时候我俩接到一个新任务,去检查一下火区内的一个手机信号塔是否安全。斯塔福德立刻兴奋起来,二话不说便开着小车出发了。信号塔位于一片已经烧完了的火场的正中间,周围一大片草地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黑色的焦炭,以及一堆堆冒着烟的牛粪,说起来没啥危险。但因为需要冲进浓烟滚滚的火场,感觉还是有点刺激的。
一进火场,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志愿者们都不戴口罩。一来火场里的温度非常高,戴口罩肯定会不舒服;二来火场内的氧气浓度很低,不戴口罩都感觉呼吸困难,戴上口罩肯定会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死于野火的人都是死于缺氧而不是直接被火烧死的。至于说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大部分危害来自燃烧后产生的各种比PM2.5还要小的有毒气体和臭氧,医用口罩肯定是防不住的,大概只有防毒面具才管用。
确认信号塔安全之后,我俩又接到一个新任务,去位于上风口的一处尚未过火的草地上点火,加快火势的推进速度。这个差事肯定是斯塔福德最喜欢的,但因为我是新手,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我俩再一次开进火场,来到指定地点。斯塔福德从车上拿下一支滴火枪,用打火机点燃了一片草叶,再用这片草叶点燃了滴火枪的枪头。这种枪里面装满了汽油和柴油的混合物,用阀门来控制滴油的速度,保证枪头上永远有一簇小火苗在燃烧。那个枪头很像一把勺子,正面是火苗的位置,背面可以放在草地上拖行,所以我只要让枪头的背面着地,然后拉着走就行了,非常容易。
因为害怕被烧,一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倒着前进。但很快我就明白只要我顶着风走,火是烧不到我的,便转过身子拖着油瓶大步朝前走。就这样走了一段路之后回头一看,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只见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火线,最先着火的地方已经借助风势烧出了100多米远,那场面堪比好莱坞大片。

经过这次实践,我立刻明白了风对于计划火烧的意义。如果没有风的话,一来火势蔓延得不够快,工作效率肯定不高;二来无风天气很容易发生风向不稳的情况,而对于放火者来说,最怕的就是风向不定,那样的话很容易被四处乱窜的火苗烧到。今天的风速大概是每小时10英里,不快不慢正合适,风向也非常稳定,所以我俩只要站在上风口就一点也不用担心被火困住。
下午3点的时候,红蓝两队终于在177号高速公路会合。这是计划中的起始点,因为那天刮的是东北风,高速公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大火则借助风势迅速烧遍了整个区域,一直烧到我们上午预先开辟出来的防火带为止,火势的蔓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奥尼尔告诉我,今天我们一共烧掉了640公顷的草地,可谓战果辉煌。
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为了防火,就把这些原本可以喂牲口的草料一把火烧掉,究竟值不值?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孔扎草原的历史开始讲起。
孔扎草原
下午4点左右工作结束,布莱尔领着我参观了研究站附设的一个面向公众的科普展厅,顺便给我介绍了孔扎草原的历史。原来,这片草原属于北美大平原(Great Plains)的一部分。这块大平原南北长3200公里,东西宽800公里,总面积高达300万平方公里(不同学术机构的估计数字略有差别),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这块地方在3亿年前还是海洋,在板块运动的驱动下逐年抬升,终于变成了现在的陆地。冰河时期这里气候寒冷,地上植被以北方森林为主,草只能在松树和云杉的夹缝中勉强存活。就这样坚持到了大约1.5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温迅速回暖,北美大平原变得越来越干旱,降雨量不足以支持森林的生长,但降雨量又没有低到沙漠的程度,于是这块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从北方森林变成了草原,整个转换过程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导致这一转变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风。顾名思义,北美大平原地势相对平缓,常年强风肆虐,还是龙卷风的高发地。不过,与其说大风刮倒了大树,不如说大风催生了大火,把树苗烧死了。正如前文所说,草的竞争对手不是草食动物,而是树木和灌木丛。它们生得高大,遮蔽了阳光,这就相当于切断了草的口粮。好在草比树更耐寒也更耐旱,所以气温很低或者降雨量不足的地区是草的主场,树木没有机会。
但是,在那些气温适宜降水充足的地方,树就占了上风。而草唯一的武器就是火,它们把自己进化成火的燃料,通过一场场雷击火烧死幼小的树苗,从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北美大平原气候干燥,风势迅猛,所以火烧得特别旺盛。于是草就在火的帮助下战胜了森林,成为大平原上的优势物种。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C4光合作用的出现。最早的光合作用大约出现在25亿年前,当时的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远比现在要高得多,所以最早出现的光合作用类型是C3。如今地球上绝大部分植物都是C3型的,其特征就是更加适应过去的高二氧化碳环境。大约在3000万年前,一种草进化出了C4光合作用,对二氧化碳的利用效率比C3要高,所以这种草更加适应现在的低二氧化碳浓度环境,其光合作用效率要比大部分C3植物高。C4玉米的产量之所以要比C3小麦和水稻高得多,原因就在这里。
C4草因为光合作用效率高,产生的生物量也大,这就为火提供了更多的燃料,于是C4草原便越烧越旺,C4草也因此而越长越高大。北美大平原上的草最高能够长到3~4米高,甚至可以把马都藏进去,所以这块孔扎草原又名高草草原(Tallgrass Prairie),是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当然了,这里见到的牛是北美野牛(Bison),羊在这里是见不到的,可以用马鹿(Elk)来代替。但这两个物种并不是这里最早的主人,这个角色必须让位给体形巨大的猛犸象、乳齿象、大地懒和大河狸。这些行动迟缓的食草动物引来了一群凶猛的猎手,这就是人。北美原住民大约在距今1.35万年前来到了北美大平原,只花了不到1000年的时间就把这几种大体形的食草动物猎杀殆尽,如此之快的灭绝速度仅用气候变化是无法解释的。
这些原住民除了弓箭和梭镖之外,最常用的武器就是火。他们发现火烧过的草地会长出很多动物们爱吃的嫩芽,于是他们会先通过烧荒的方式把动物们吸引过来,然后用火将其围困并杀死。就这样,北美高草草原在自然之火和人类之火的双重辅助下迅速扩张,大约在距今8000年左右时达到了面积最高峰,总面积高达68万平方公里。
当年北美殖民者在西进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片大草原,却将其命名为美国大沙漠(Great American Desert),因为在这些西欧人眼里,只要没有树的地方就是沙漠,毫无经济价值。其实草原的经济价值是非常大的,因为人类驯化的几种主要粮食作物原本都是草,最常见的牲畜也都是草食动物。好在这些白人殖民者终于明白了过来,开始在大平原上试种小麦,结果大获成功,于是这片地方逐渐变成了美国的粮仓,绝大部分草原都被开辟成了农田或者居民区。但与此同时,曾经高达5000多万头的北美野牛种群如今只剩下了20万头,它们的位置被人工饲养的牲畜所代替。
“早年的殖民者太过依赖欧洲经验,忘记了人类最早就是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进化出来的。”布莱尔补充说,“我曾经有机会去南非做访问学者,一见到那里开阔的稀树草原就觉得自己回家了,那种熟悉感和亲切感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
只有一个地方逃过了这股农业化的浪潮,这就是位于堪萨斯州东部的燧石山(Flint Hills)。顾名思义,这块土地盛产燧石,这是一种硅质岩石,质地极其坚硬,经常被原住民拿来制造弓箭的箭头。因为燧石的存在,这块地方没有被冰川运动和随后的风雨侵蚀彻底磨平,而是留下了一片广阔的丘陵地带。崎岖的地形不但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而且燧石和石灰岩混合的土层会把锄头弄坏,导致耕作变得非常困难,于是殖民者们放弃了耕种,把燧石山划为牧区,允许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定期放火烧荒的传统,这才保住了这片草原。
今天的燧石山是目前保留下来的结构最为完整的北美高草草原,总面积约为2.57万平方公里,仅为鼎盛时期的4%。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原,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草原生态,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罗伊德·胡尔伯特(Lloyd Hulbert)早在1956年就开始寻找研究基地,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将这片草原保护下来,不被过度放牧所破坏。1979年,一位名叫凯瑟琳·欧德维(Katharine Ordway)的慈善家出资买下了一块面积约为366公顷的土地,将其赠予了胡尔伯特。这位欧德维的父亲是美国著名的3M公司的总裁,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之后她又陆续买下了更多的土地,最终连成了一个总面积约为3487公顷的草原生态保护区。她唯一的要求就是用印第安原住民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区,这就是孔扎草原的由来。
今天的孔扎草原是由堪萨斯州立大学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共同拥有的自然保护区,而它要保护的对象就是草原本身,因为气候变化使得美国中部的降雨量逐年增加,如今的年降雨量已经达到了845毫米,足以支撑树木的生长。
“如果不加干涉的话,孔扎草原只需30年就会完全变成森林。”布莱尔对我说,“我们必须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孔扎草原,否则的话整个北美地区的草原生态系统很可能就将不复存在。”
“你所说的干涉主要就是指人工火烧吧?但环保组织不是一直都在教育我们不要干涉大自然吗?为什么不能任由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发展下去呢?比如既不主动点火,也不再扑灭闪电火?”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孔扎草原的环境变化大都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降雨量的增长幅度还是气温升高的速率都远超自然节律。”布莱尔回答,“我们实行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就是在模仿大自然应该有的外部环境,以此来弥补人类行为造成的破坏,帮助孔扎草原恢复生机。”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录,以及对持续拍摄了60多年的空中老照片的分析,科学家们发现孔扎草原在1859年时仅有5公顷的森林,1939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159公顷,2002年更是增加到了274公顷。即使1859年的数据不那么可信,也说明孔扎草原的森林覆盖率在过去的63年里增加了72%,这个速度不能仅用气候变化来解释,而是另有原因。
布莱尔为我列举了几个可能的原因,每一个都和人类活动有关。
首先,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不仅加剧了气候变化,还增加了树木和灌木丛这些C3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而孔扎草原原有的长草则大都是C4植物,这些草的光合作用效率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不会受到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影响,所以人类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相当于间接帮助了树木,削弱了草的竞争力。
其次,人类的开发活动将原本连成一片的大草原分成了很多区域,彼此之间以道路或者房屋分隔开来,导致现在的森林大火无法像以往那样顺利推进。换句话说,以前每一次闪电火都有可能烧遍整个大草原,如今的草原大火却因为各种环境限制而无法持续扩散,所以计划火烧的目的就是弥补自然火的不足,甚至今天的草原大火强度即使在有了计划火烧之后也仍远小于人类定居之前。当然了,现在的人口密度也不允许野火像过去那样无节制地扩散,而计划火烧这种低强度小范围的野火很可能是今天人类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补救措施。
再次,人类对肉食的需求促进了畜牧业的繁荣,过度放牧会减少草的蓄积量,这就相当于减少了火的燃料,进一步降低了野火的强度。比如我们今天的计划火烧涉及一处小树林,但因为地上的草太少,火烧不起来,就连位置很低的树枝,以及大部分林间灌木丛全都完好无损。
最后,人类普遍喜欢阴凉,会在房前屋后种上很多树木或者灌木丛,这个行为相当于帮助树的种子更好地扩散,进一步加速了孔扎草原的森林化。
我曾经问过《火之简史》的作者派因同样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原住民的烧荒行为,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至少一万年,大自然也已经完全适应了计划火烧。如果我们突然停止放火,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野火的强度不足,大自然在短时间内都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参观完毕后,布莱尔开车送我回旅馆。当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但空气中还是能闻到一丝烧火的味道,能见度也不如想象中的好。布莱尔告诉我,这是因为整个燧石山地区的牧民都开始计划火烧了,所以每年春季这里的天空经常都是灰蒙蒙的。
车子一开出孔扎草原,路边立刻出现了大片的农田,很多田块上堆满了秸秆,没有火烧的迹象。“我曾经采访过派因,他认为应该恢复过去农民烧秸秆的传统,这样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不知你怎么看?”我问布莱尔。
“我不同意这么做。一来堪萨斯的农田太多了,如果允许烧秸秆的话空气质量就更糟糕了;二来我们正在全州推广免耕法,需要秸秆还田,让土壤中的微生物代替火来完成分解秸秆的任务。这么做肯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所以免耕法在实施的头几年里效果很可能不如火烧。但只要坚持做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见到成效,因为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这才是健康土壤的标志。”
布莱尔的回答让我意识到火并不是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万能药,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从长计议。那么,人类用计划火烧帮助草战胜了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否一定是一件好事呢?
树草之争
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第二天还要去烧另一块草地,但上午接到堪萨斯州政府的紧急通知,因为天气预报预计两天后可能会刮大风,所以全州禁止计划火烧。于是布莱尔决定开车带我去孔扎草原逛一圈,让我能深入了解野火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布莱尔是“长期生态学研究项目”(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LTER)孔扎研究站的负责人,该项目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资助的一项生态学研究,重点关注人类行为的长期生态影响。孔扎研究站的主要研究对象无疑就是计划火烧,研究人员把整个孔扎草原分成了50多个试验地块,相互之间由一个个分水岭(Watershed)分隔开。这些单独的试验地块分别采取一年一烧、两年一烧、四年一烧和二十年一烧等多种处理方式,以此来比较不同的火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布莱尔先带我参观了一个一年一烧和多年不烧的对照试验地块,一年一烧的区域自然全是草地,紧挨着的那块多年不烧的区域则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枝叶密到不用砍刀根本走不进去的程度。
“这种灌木名叫山茱萸(Dogwood),是这里最常见的入侵物种。这种灌木一旦成形之后就不怕火了,烧过之后很快就能再发新芽,是孔扎草原最大的威胁。”布莱尔对我说,“山茱萸长得特别密,挡住了阳光,所以林下植被非常稀少,草原上最常见的四种野草全都无法在灌木丛下正常生长。”
布莱尔所说的四种常见野草分别是大须芒草(big bluestem)、小须芒草(little bluestem)、印第安草(Indian grass)和柳枝稷(switchgrass),它们全都是北美野牛和马鹿爱吃的草料,尤其是富含蛋白质的嫩芽更是动物们的最爱。研究显示,如果在火烧过的地块放牧的话,牲畜的长膘速度要比吃普通长草饲料快10%~12%,原因就是过火的地块上嫩芽特别多。
“这些长草的根系特别发达,不但有纵向生长的根须,还有很多横向生长的根茎(rhizome),它们合起来组成了一层细密的草皮,像一层被子盖在土壤上,能够防止水土流失。”布莱尔用手拨开一丛杂草,指着草根下方的土层对我说,“这层草皮又厚又硬,甚至影响到了农民的耕作,这是孔扎草原至今未被开发成农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布莱尔又带我参观了另一处试验田,这是一项持续了40年之久的倒转实验,实验对象是两块紧挨着的试验田,中间被一道低矮的分水岭隔开。其中一个地块连续烧了20年,另一个地块则完全禁火,可想而知前者20年后依然是草原,后者则变成了林地。然后,研究人员把处理方式倒转了一下,让那片林地每年过一次火,而那片草地则严禁放火,就这样又持续了20年,情况几乎颠倒了过来。当初那片草地如今长满了深绿色的灌木丛,而当初那片林地则变成了高草草原,只是因为季节未到,草叶依然枯黄。
“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那片烧了20年的地块看似已经恢复成了草原,但如果你走进去的话就会发现那里仍然生活着大量山茱萸,它们坚硬的根茎会让你下不去脚。”布莱尔对我说,“这个实验结果证明每年一次的火烧只能限制灌木的生长,但却难以彻底杀死它们。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停止火烧,这些灌木便会迅速扩张开来,再次把草原吞噬掉。”
布莱尔的课题组进行过好几个类似的试验,证明这地方原来实行的每四年进行一次的计划火烧强度不够,至少要提高到每三年烧一次的频率才能有效防止森林和灌木对草原的侵蚀。而且一旦开始计划火烧就不能停,因为一旦停止火烧,让树木和灌木站稳脚跟,再来放火就烧不死它们了,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加极端的措施,比如人工清除或者施用具有针对性的化学药物才能奏效。
望着眼前这一绿一黄两个地块,我仿佛看到了树和草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厮杀,只不过这场你死我活的竞争持续了20年,难怪英国广播公司(BBC)拍的那些植物学纪录片都喜欢采用延时摄影的方式把时间加速,因为只有这样普通观众才能明白植物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动物,以及生态学为什么会被称为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
“这个实验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开展长期生态学研究,因为很多生态变化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来。”布莱尔补充道,“最近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我们这个项目肯定会受到影响。如果真的被砍掉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草原生态学研究将会倒退很多年,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有大约四亿公顷的草原,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0%,欢迎你去中国做研究。”我对布莱尔说,“不过中国的环保组织似乎不太重视草原,更喜欢种树。比如很多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都会鼓励民众去西部沙漠和戈壁滩上植树造林,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环保。”
“森林当然很好,但千万不要过高地估计了它的生态价值,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树。”布莱尔回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草原的物种多样性都会更好一些,一块草地所能养活的动植物数量要比森林多。”
就拿孔扎草原来说,这里有700多种植物,其中有70%来自非禾本类开花植物(forbs),它们是孔扎草原的夏天之所以如此美丽的主要原因。这些植物开的花能够吸引大量传粉昆虫来此生活,它们的种子也能养活很多小型动物,但它们全都无法在树林里生活,因为林地的光照不足。
同理,包括野牛和马鹿在内的大型食草动物肯定也是更喜欢草原,而孔扎草原的旗舰物种草原松鸡(prairie chicken)是不会在森林里抱窝的,如果孔扎草原变为森林的话,这种草原松鸡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生活在这里的其他200多种鸟类的日子也肯定好过不了。
如果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果,那么因就是生态系统的改变。森林和草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从植被结构到野火燃烧方式,再到水和营养物质的循环模式都很不一样。比如,布莱尔和他的同事们刚刚在2024年11月出版的《水文学杂志》(The Journal of Hydr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孔扎草原的溪水流量越来越小的原因。原来,随着树林和灌木丛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夏季雨水被树木的根系导向了更深的地层,而大型木本植物的蒸腾作用也消耗了比草更多的雨水,于是留给草原的地表水就越来越少了。这个变化相当重要,因为孔扎草原本就不是一个雨水充足的地方,稍不留神就会遭遇旱灾,溪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相当宝贵的资源。
孔扎草原的案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植树造林运动都是对环境有益的。2024年2月1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论文,批评了德国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于2011年在非洲发起的“波恩挑战”(Bonn Challenge)。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30年时恢复3.5亿公顷的非洲退化森林,听上去似乎是一项很不错的环保项目。但论文作者指出,目前非洲国家认捐的造林土地面积当中一共有7010万公顷(占已承诺总面积的52.5%)原本并不是森林,而是草原或者热带稀树草原。事实上,草原和稀树草原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40%以上,原本是一种很常见的陆地生态系统,在这些地方强行植树不但不会保护环境,甚至有可能破坏这些地区原有的生态系统,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全面丧失。
说起来,非洲的稀树草原是人类的摇篮,当初正是由于森林的退化,才让原本生活在树上的猿人祖先们学会了直立行走,并解放了自己的双手。早期人类的狩猎采集活动大都是在草原上完成的,现代人的绝大部分粮食作物全都驯化自野草,畜牧业自然也离不开草原。相比之下,古代的森林反而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可怕的存在,尤其是热带雨林,在先民眼中是一个充满瘴气的恐怖之地。
但是,今天的森林却成了环保人士最喜欢歌颂的对象,世界各国都把森林覆盖率当成衡量环境是否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2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三个百分点,这一点曾经被很多人诟病,认为这是中国的自然环境还不够好的证据。其实美国的森林覆盖率也仅为30.8%,在发达国家中算低的。而孔扎草原所在的堪萨斯州的森林覆盖率仅为5%,在美国的50个州中排名倒数第四位。但我丝毫没觉得这里的环境比其他地方差,因为到了夏天大草原和森林一样都是绿色的。
森林之所以后来居上,甚至成为高品质生活的象征,一个原因是树木可以作为建筑材料和造纸原料,比草的用途更广泛。另一个原因是树木体形更大,可以为城乡居民提供遮阴场所。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气候变化,因为民众普遍认为森林是最好的碳汇。
“如果单独比较一块草地和一块林地,那么林地储存的碳确实有可能更多些。但树木的碳大都储存在地上部分,一旦树死了或者被烧掉就又全都释放到空气中去了,很不保险。”布莱尔对我说,“但孔扎草原的长草有60%的生物质是储存在地下的,其根系相当于一座地下森林,这部分碳非常保险,几乎不会丢失,所以草才是更可靠的碳汇。”
可惜的是,大部分人缺乏这个认知,仍然相信森林才是最好的碳库。很多大公司试图通过植树造林来抵消自己的碳排放,没有考虑到树是很容易死的。菲律宾的吕宋岛曾经在2012年举办的一场植树活动中创下了一小时种下100万棵红树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2020年再去调查时发现只有不到2%的树苗成活。土耳其政府则在2019年举办的一场全国性的植树活动中创下了一小时内在干燥土地上种下30万棵树的新世界纪录,打破了不丹在四年前创下的旧纪录。但两个月后土耳其森林管理局派人前去复查,发现90%的树苗已经死亡。
当然了,更大的问题是山火,一场山火会让储存了几百上千年的森林碳汇在一夜之间全部灰飞烟灭。2023年底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了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篇论文,指出2001~2022年间全球超级森林大火一共排放了339亿吨二氧化碳,比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在同一时期内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还要多。更糟糕的是,这期间全球的年均森林过火面积相当于同期人工林年均增长面积的11倍,这就意味着自然林火抵消了植树造林在增加碳汇方面的所有努力。
同样,碳汇也是很多人反对计划火烧的理由,但他们忘记了气候变化只是影响环境健康的诸多因素之一,而衡量一个生态环境是否健康的黄金标准并不是碳汇的多少,而是生物多样性的高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UCB)曾经在北加州的森林里进行过一项为期20年的计划火烧对照实验,结果证明计划火烧能够提高树木的抗逆性,增加抗旱抗虫的能力,对生物多样性也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加州森林已经有长达半个多世纪没有着过火了,导致树木的密度特别大,计划火烧很容易失控,于是研究人员在几个地块采用了先人工剪枝再计划火烧的措施,结果证明比单独烧的效果还要好。
另一个有计划火烧需求的地方就是美国的东南部,这里原本盛产长叶松(longleaf pine),这是一种叶子很长、透光性很好的松树。这一特征使得长叶松林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持得非常好,养活了大批印第安原住民。白人殖民者因为造船的需要,无节制地采集松节油,导致大批长叶松死亡。殖民者确实补种了很多松树,但却选择了一种速生的品种,于是这片地区的长叶松数量大减,生物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破坏。美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恢复长叶松的种群密度,研究表明最好的办法就是计划火烧,因为长叶松比其他那些速生的松树品种更耐火。
我原本计划去佛罗里达州的奥克弗诺基(Okefenokee)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参观由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负责实施的计划火烧,但因为天气一直不合适,火烧行动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行程。该保护区的负责人迈克尔·拉斯科(Michael Lusk)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以往每个火烧季平均要烧12次左右,但今年因为极端天气太过频繁,迄今为止只烧过两次,而今年的火烧季只剩下三个月了,很有可能完不成预定的火烧任务。
无独有偶,堪萨斯的火烧季也因为极端气候的缘故而不得不减少了火烧的次数。就在我离开孔扎草原的第二天,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美国中部大平原,导致至少18人死亡。这场大风还引发了无数场山火,仅在俄克拉何马这一个州就发生了超过150场野火。
“最近这几十年来,孔扎草原的整体气候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极端天气明显增加了。”布莱尔在临别前对我说,“这个变化让计划火烧变得越来越困难,不知道我们的研究还能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结语
计划火烧到底好不好?野火对空气的污染和增加的碳排放是否能抵消它对生态的益处?能否用其他更加温和的方式替代计划火烧?没人知道答案。
派因认为,人类对野火生态学的认知还远远达不到要求,没人敢打包票说目前的策略肯定是对的。但我们应该鼓励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管理机构尝试新的方法,而且要允许它们犯错,否则的话人类永远不会进步。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强教育,让民众慢慢学会接受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
文章作者


袁越
发表文章53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203人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