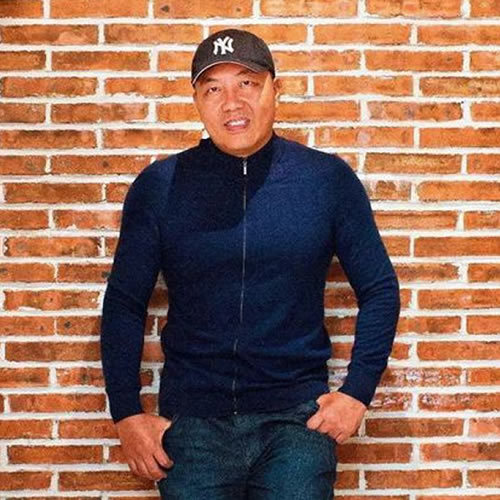不日记八十七:微澜(并序)
作者:罗成
2021-08-14·阅读时长7分钟
20218月12日 星期四微澜
本文该有个副标题,——《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房伟)摘记。
今年的“五一”也许算得上好。因为不必要说的原因,我们全家可以全无挂碍地出游一趟。虽然明知道赶了个热潮,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平时,有各种琐屑事,总之离不开。今年终于可以走了,心情觉得舒爽。而能够和全国人民同一时间出游,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们选择了西安,虽然对西安的热有所畏怯,不过因为对兵马俑和大雁塔充满了想象,所以还是很兴奋,前一天就先想起了当年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时间久远,对片子的印象,早已剥离了当年对张艺谋滥俗的诟病,却很多了几重好感,或者说亲切。时间,向来就是最有力的雕塑师。
我们是在五月一日的中午到达西安北站的。西安果然很热,而且站前广场正在维修,道路逼仄坎坷,四围人声扰攘,就有些心烦意乱,似乎对这一程,不敢太抱期待。但在路上途经大荔,还是很高兴。大荔,就是著名的“左冯翊右扶风中京兆”里的左辅,在去往古都的路上令人颇多想象。高铁出运城不久,就到大荔。虽然事前心里有所预备,但是听到报站,眼前还是陡起了滚滚飘渺的烟尘,云雾里许多宽袍大袖的人步履雍容,画片一样影影绰绰,络绎不绝。
吃过午饭,就去了大雁塔。想象固然很好,但总不如现实来得无情,塔比想象中依然低矮了不少,而且不见小雁塔遥遥相对,未免显得寂寞。寂寞从来与人多少没有什么关系,于人如此,于塔,也仍然如此,也许于山,于水,于园林,于落日,也都如此。不过大体还算不走样,可聊做安慰。
五月二日一大早往临潼赶,一路上旅游巴士不断,到了委实车多如流,人多如蚁。如果所记不谬,唐宛儿(《废都》)是从临潼来的吧?那一个妙人,也曾经被裹挟在这挤挤挨挨的人流中吗?这才突然悟到,为什么昨天在大雁塔,并没有想像中的感觉了。
比如今天天气薄阴,所谓天公作美,然而,市声如潮,我对大家苦笑,说“脑瓜疼”。停车场门口私家车拥挤,游人在人缝车隙里穿插游走。兵马俑广场更甚之,有自驾游的一家到了门前买不到票,全家人一脸愁容,几口叹气。直到后来离开临潼,我心里还挂念着那远道而来的一家人,是不是依然在焦虑。景点周边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有时远甚于景点本身,这正如对方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状况,有时远甚于自己要结婚的那个他(她)。现实生活里,椟,很多时候真的可以掩盖了珠。闹市中取静,人声里读书,真是需要定力的。于是,我挤在人群里想象那些兵马在被做成俑以前,是如何在当年的战场上驰突冲杀,在路上想象大雁塔中的藏经,是怎样满足了阿傩、迦叶的索贿,方才拿到手。原来,唐王的一只紫金钵盂竟然真的就抵得上了九九八十一难,和一路风刀霜剑,妖魔鬼怪。
这样想着,我看到秦俑村口那尊雕工粗劣的秦始皇造像,唯有苦笑了,嬴政,你对后人肆意打乱你的灵魂清净,怎样想,又如之何呢?如果无奈,那么宿命论可以行矣。我的视线从秦始皇的冠冕上方越过,对远方的墨绿色的山线充满了想象,——又是想象,又只能靠想象了——,对,是骊山。“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长安晚出袅唫鞭,税驾骊山一怅然”,“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是啊,华清池,还有捉蒋亭。歌中唱的好呀,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直到五月三日,来到青龙古寺,心情才有所平静,想象反而更深。寺不大,车到门前,扑入眼帘的就是青龙寺古朴雅致的大门。因为去得早,游人不多,石阶上零零星星有一些早练的市民,跳绳舞蹈,很增加了烟火气,让人觉得亲切。
三组石阶上去就是那座复建的古楼。
青龙寺据说得名于萧何修建未央、建章、长乐三宫,后惠帝刘盈时大规模修建长安城,遮断了小青龙与泾河龙女含情相望的故事。这么说来,就已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悠悠岁月中,日本的“入唐八僧”摹学汉唐文化,传先进思想于东瀛是光彩的一笔。寺中的后院,至今还有空海受教于惠果大师的铜雕,那一摸顶,慧根打开,真言初成。听人介绍,每到阳春三月,寺院内樱花相继盛开,春色满园,姹紫嫣红,是赏樱的好去处。院子的一角,有不算太高的一座钟楼,下面雕刻着不少日本捐建者的名字与籍贯,让人有距离感。据说,楼建于1995年,上面的大钟为“中日友好和平之钟”。这当然是美好的祈愿。
其实,祈愿,往往来自于不易得或者根本不能得。比如秦始皇的长生不老,比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又是无奈的祈愿,只能用“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来自我安慰。所以,也正如前一晚逛的闹市叫永兴坊,正在于盛世不再,唐代井坊早已消散,一家卖泡馍的俊朗的老板,头裹着白羊肚手巾,唱的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晚上逛回民街而不得兴,因为恰值大雨如天河倾泻,吃了一次泡馍确是由于无法再前行,反觉满口滑腻,味不尽佳。所谓大唐不夜城,也不过是赚足人们银锭的商业街吧。后来回忆,觉得这一次西安之行,只有那古寺,古寺的塔楼令人意有不尽。
古寺南临公路,北靠灞河。想象里,灞桥烟柳,摇摇曳曳,一带烟树下,有许多远行人洒泪登程。好吧,你知道塔楼上的牌匾是什么吗?我对那古原,久多驰想:莽莽苍苍,渺渺无边,在灞河边折柳上路的断魂之人,被一乘小车载往他乡,身影渐渐隐没于黄昏的浑浊的天色里。人们失意时,落寞时,都会站在那莽原上向远方凝望,把不如意的叹息声和无边遥远的思绪,飘散在远古的柳色里、骊山下、空气中。
据记载,古原得名于西汉的乐游苑。“汉宣帝立乐游庙,又名乐游苑。登上它可望长安城。乐游原在秦代属宜春苑的一部分,得名于西汉初年。《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起乐游苑’。汉宣帝第一个皇后许氏产后死去葬于此,因‘苑’与‘原’谐音,乐游苑即被传为‘乐游原’。对此《关中记》有记载‘宣帝许后葬长安县乐游里,立庙于曲江池北,曰乐游庙,因苑(《长安志》误作葬字)为名。’”(摘自若愚博文《西安乐游原上青龙古寺》)
查阅其它资料,若愚所记,大体不差。这么说来,爱游赏的李太白应该在这里白衣飘飘过,王摩诘大约是从这里踟蹰着去了他的辋川山庄的。高适,岑参自不必说。杜少陵一个人坐在曲江边,感叹“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他对着曲江恳切地说,“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他醒时来,醉时来,赌气说“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可是依然觉到岁月逼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池北的乐游,从“苑”到“原”,一字之易,满眼繁华,转眼间做了个哗啦啦大厦倾颓,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天地大雪苍茫里,宝玉大红的斗篷远去是这样,被誉为“红楼之祖”的《金瓶梅》也是这样,到吴月娘梦见“普静师幻化孝哥儿”去了,热闹也罢、败落也罢,一切变成了一场空,滚滚喧嚣,尘埃落定。
李义山心情荒凉,驱车登上古原,回首可见繁华热闹的长安城,转身远眺却是红日已渐渐西垂,目光看透几千年起起落落,风聚云散,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唐这轮大太阳,固然很好,终于也要下山了。秦汉岂不亦如此矣!原之为古,一己之不适,瞬间连接了千古之悠远。我一直觉得,陈伯玉曾经在初唐登高,因为看穿了古今,那泪落得令人感佩,令人肝肠寸断。而到了晚唐李义山这一望,所见就仅剩空寂了。好呀,唐之盛,在于中有李杜,有天宝大历,还在于首有陈伯玉,尾有李义山,时间上首尾两相呼应,空间上一在天之北,一在地之中,唐朝这一篇大文章,真是做得辞藻华美,结构谨严,起于哀悯,结于空寞,应该是时间得意的一章。
一出大戏,好就好在说完了所有因果里的根根由由,结束上的飘飘渺渺。
这一路,从上高铁开始,每有余暇,我就看一本书。在大巴上,安静时不看,喧闹时看,车开时不看,堵车时看。行车看书,怕头晕,更怕耽误了沿途的好景致;堵车时看,不想浪费掉一点好时光,也让书中的世界宽解我说,堵车本是世间常态,在意它,你就输了。人生岂不正是如此,在意它,嘿嘿,你累不累!等我要踏上归程,在一车人的热闹声里,看过了五千年起落时,也正好读完了“王小波”。再眺望骊山,我仿佛看见了几千年的云烟翻腾,登乐游原,却让我又把这滚滚匝匝的烟云看了个透彻:原来,书中也罢,人间也罢,所有自得、所有繁华莫不如此。
我原本本能地对一切所谓“好”,保持警惕,这正如王小波对托尔斯泰式的道德训诫和忏悔保持警惕一样。这一行,又让这种紧张有所松弛。所以,回来了,回归日常世俗,这一行程本如微澜,转瞬就会复归平静。这对于人们,对于我,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然而,真得没有改变么?对于人,一切也许真得就是瞬起瞬逝的小波涛,然而也许变化就在这不觉不见之中已经发生了。
这对于我的阅读王小波,可算得一场笺注吧。
注:摘记部分略。
文章作者

罗成
发表文章1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3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