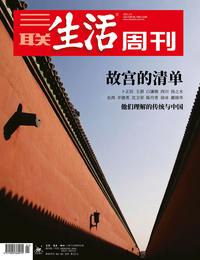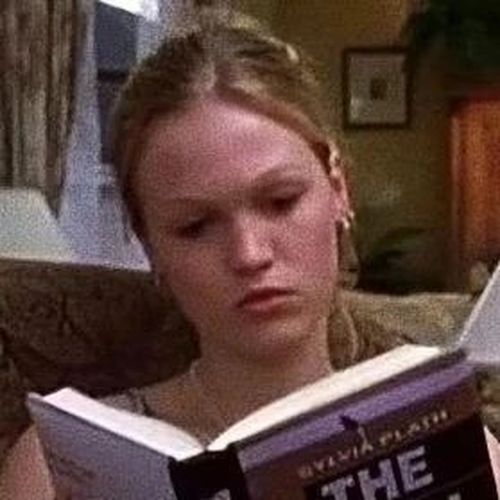故宫藏画与《背后的故事》
作者:徐冰
2020-12-30·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228个字,产生1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鹊华秋色图》,元,赵孟頫绘
先从我手头正在创作的《背后的故事:鹊华秋色图》谈起。
我一直喜欢赵孟頫的画。《鹊华秋色图》是他42岁时,摆脱官场困境,从济南回湖州后,为祖籍济州(今济南)的友人周密缓解思乡之情所作。画上题跋显示,他先向周密“说齐之山川”语言不足“乃为作此图”。画上两山分别为齐州一带的鹊山和华不注山。赵孟頫将两山名合为画名。
上面关于《鹊华秋色图》的信息都属于知识范畴,但在工作室一进入创作,就会面对知识之外的内容了,这也就是我最感兴趣的重新发现的部分。说实话我这些天最纠结的就是:是把布满画面的那些题跋、印章都复制出来?还是只恢复赵孟頫画完时的原貌?开始时我决定,只把赵孟頫的部分恢复出来,让今人感受画家原本的意图。但当我与助手认真完成这部分时,把工作样稿和多余的材料清理掉后,画面就像刚理过发的人,怎么看怎么不是赵孟頫这幅画的感觉。我试着再把工作样稿随意贴回“宣纸玻璃”背板上,我发现,多少有点赵孟頫的感觉了。当我试着把更多的参照稿或碎纸片随意贴满空白处时,《鹊华秋色图》的感觉才出来了。
结果我发现,把细节还原得再像也无济于事,这让我意识到,一件名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内容里,画面细枝末节的信息只占很少的部分,而更多是这幅画的气氛,或者说是一个气氛的符号。对这气氛的记忆有时甚至还包括画面气氛之外的气氛。你回想一下,在卢浮宫看《蒙娜丽莎》或在故宫看《千里江山图》,你挤在人堆中使劲地看,离开后留在记忆中的是什么呢?文字学证明过,读字作为读符号,主要是对外形的识别。汉字更是如此,每个字都有一种气氛,或繁密或疏简,或横势或竖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在简、繁体转换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人,繁体字能认,但真让你写,有些就写不出来。因为对外形有印象,但繁密的一堆是由那些笔画搭出来的,就含糊了。这有点像读已成为符号的名画的“氛围”。而这氛围是由画家本人与作品日后的命运,共同创造的。
《鹊华秋色图》也许是被后人题跋盖印最多的作品了,不算引首、前后隔水的部分,仅画面内,除赵孟頫本人的题跋以外,后人共加了4篇题跋、58个印章。这让我创作中纠结于对中国题跋文化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绘画可以在作品制成后,遇到知音或落入陌生藏家之手,仍然可以在画面上题跋盖印?并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此已有学者做过专题研究,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我在动手做作品时的思考:为什么我用《背后的故事》的方法可以复制中国古代绘画却不便复制西方古典写实绘画?

《背后的故事:鹊华秋色图》,徐冰作品
其实,中国绘画如同写字,画家基本上是把所画景物平均摆在画面上,视重要与否、远近大小做适合生理视觉舒适度的调整,其布局技术直白说是今天的“平面设计”,大小疏密要摆得讲究。而装置《背后的故事》的大玻璃,从空中穿过,如同一块巨大的感光底片,影印出由原作者整理过的画面。而原作者或后人题跋、再跋、补跋,是利用平面留白处重新摆布构图,找到画面新的平衡或不平衡,同时也为下一位好事者留出了余地。
如此一幅画,平衡,打破,再平衡,再打破……像是始终留着生长的空间。这又像写汉字,下一笔根据前面笔画位置、笔笔生发,每一笔都在打破和建立平衡关系。而西方古典绘画技术的核心要素是在“洗印照片”之前,先将画家的肉眼锁定在曝光量不变的镜头上,再按下快门。素描课上,老师总强调:“要‘眯’起眼睛看大关系,暗处要整,远处要透视缩减、推过去……”几年下来终于将学生的生理之眼改造成了金属之眼,成功地将有纵深感的三维世界转移到二维平面上,看起来还是三维的。在这种反映客观存在的纵深空间中,确实不好再写什么东西上去。我们不能想象后人能在《蒙娜丽莎》原作上题写或加盖一些东西。
文章作者


徐冰
发表文章3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106人
著名艺术家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