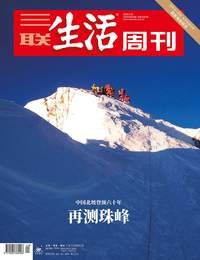末日痴迷
作者:薛巍
2020-05-13·阅读时长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716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爱尔兰作家马克·奥康纳
从《启示录》到《后天》
物种大批量灭绝、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抗药性病菌扩散……这些灾难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在临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生活竟会随时画上句号。西方人对世界末日的担忧由来已久。在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发现,在他的时代300年前,耶稣最早的追随者们陷入了末日狂热,相信他们生活在末世。他写道:“如果那时是末世,现在更是!”爱尔兰作家马克·奥康纳在《末日笔记》中说,整个西方文明,从“诸神的黄昏”到《启示录》和《路》(美国作家麦卡锡的小说),都建立在洪水和大火之上。
英国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认为,末世论在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到了现代变得更为强烈。他在《结尾的意义》中写道:“我们通常把我们自己的危机想象得非同小可,比其他的危机都更麻烦、更有趣。麦克卢汉认为,我们正处在他所谓的星际渗透的交叉点上。埃里希·奥尔巴赫相信,他的时代有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只有在这种时代,人们才能对欧洲的真实面貌获得清醒的认识,因为欧洲文明即将寿终正寝,即将被另一个历史的统一体所吞没。索罗金指出,现代历史哲学很可能会以末世论为特征。现代思想包含着很强的末世论因素。它在艺术中得到了反映,据说《格尔尼卡》反映的就是毕加索所感兴趣的中世纪的启示论。对世界末日的恐惧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一个特征,现在成了特里林所说的敌对文化或亚文化的那种现象的一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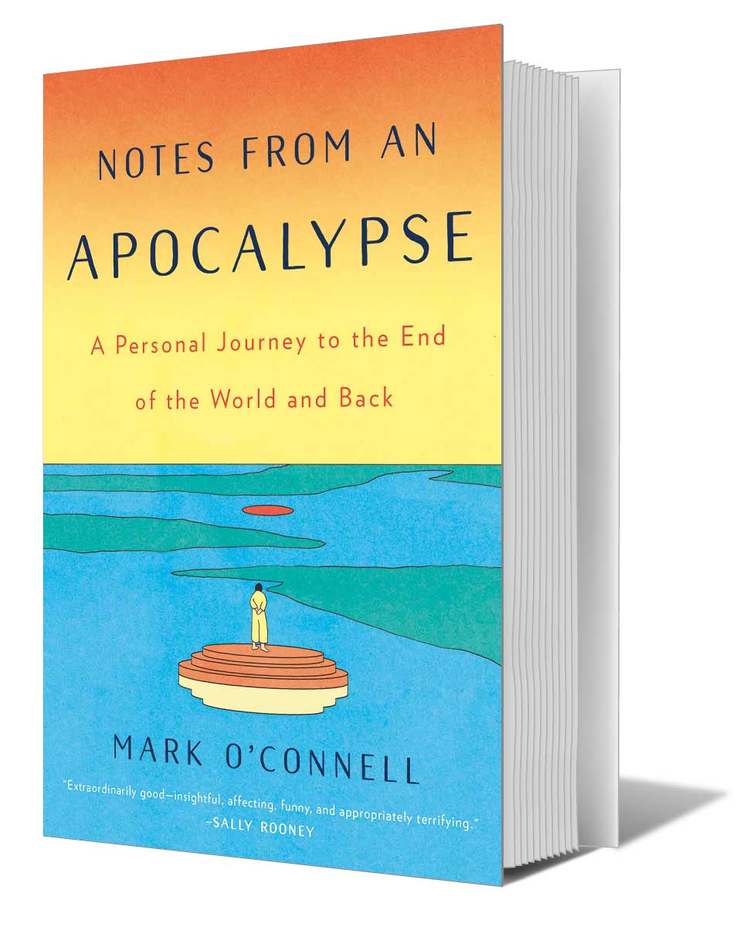
《末日笔记》
1965年,桑塔格在《对灾难的想象》一文中说,科幻电影中的幻象反映了对全世界的焦虑,并试图缓解这种焦虑。“人们已经明白,从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端,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
科幻作家戴尔·贝利意识到,世界末日每时每刻都正降临在某个人身上。他说:“我们不需要在经历过整座城市的毁灭之后才明白大难不死是什么感觉。每当我们失去某个挚爱之人时,世界末日就已经降临。”他在《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中说,世界末日的故事通常有两大类。第一类,世界毁于一场自然灾难,这场灾难一定有着史无前例的类型或规模。“头号种子选手便是滔天洪水——我们知道上帝他老人家十分偏爱这种手段——不过传染病也不乏忠实拥护者。”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冰河期的再度来临,或是另一场大旱。第二类,不负责任的人类自作孽。典型例子是洲际弹道导弹互射。
世界末日之后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强韧的个人主义者。他们自力更生,独来独往,会使枪炮,还擅长给产妇接生。在故事最后,他们总是走在重建西方文明的康庄大道上,而且这些人通常聪明过人,不会重蹈覆辙。第二类是后末日的强盗恶棍。这类角色通常成群结伙地跟那些坚忍不拔的幸存者对着干。第三类虽然跟前两类比起来属于小众,但也相当常见,他们就是悲观的愤世之徒。
奥康纳本来很悲观,但他最后觉得他对末日的担心有些矫情,“担心世界的终结只不过是担心失去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害怕文明崩溃只是害怕我不得不像那些支撑着文明的普通人一样死去,如种咖啡豆的人、制造智能手机的人。对于街头那些数不清的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文明已经崩溃了。世界的终结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反乌托邦的幻想。它就在你周围。你只需要看一看就能看到”。
文章作者


薛巍
发表文章583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4997人
江湖人称“贝小戎”、“小贝”,读书万卷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