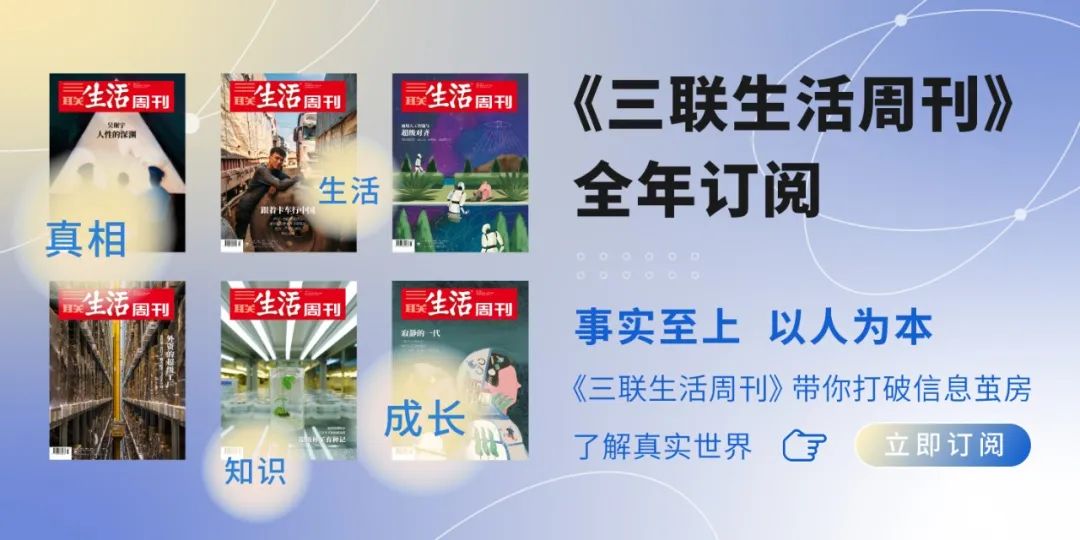“葬礼不应该在人去世几天内仓促完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7-03·阅读时长25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传统中,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亲人离世,从"头七"到"七七",复杂的仪式和大家族的团聚为丧亲者提供了认知死亡、抒发哀痛、获得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但仪式不是"化石",而是"流经当下生活的河"。传统仪式里的哀伤表达正在失去文化土壤,也正在失去大家庭这一社会结构的支持。现代人需要寻找和构建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告别语法。
记者|驳静
编辑 | 徐菁菁
在传统中,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亲人离世,从"头七"到"七七",复杂的仪式和大家族的团聚为丧亲者提供了认知死亡、抒发哀痛、获得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但仪式不是"化石",而是"流经当下生活的河"。传统仪式里的哀伤表达正在失去文化土壤,也正在失去大家庭这一社会结构的支持。现代人需要寻找和构建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告别语法。
记者|驳静
编辑 | 徐菁菁
被压缩的告别
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符号,在我成长过程中称得上是寻常。我在浙北一个村子里长大。从小我的生活里就有“棺材”这个东西。我阿太(外婆的妈妈)房间里,紧挨着她的床,就摆着一口黑棺,长年累月,阿太与它同吃同睡。阿太的房间在一楼,上到二楼,还有两口棺材,上下叠放,分属于外公和外婆。它们摆在楼梯口的空地里,和一个巨大的木箱为邻。
我家对面那幢房子住着一位唢呐先生,但凡哪一天,天还未亮,有刺耳的唢呐声将我吵醒,我就知道,接下来会有葬礼。

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枸杞岛,一处墓地正举行葬礼(视觉中国 供图)
围观葬礼,是我小时候挺喜欢的活动。跟着送葬队伍,能看到又哭又唱、扒着棺材不肯放的女人。我尤其还会留神细看葬礼上抱着遗像、身着孝衣的人,有时候是大人,有时候是小孩。那时我头脑里还有一个从来没问出口过的疑问:一个人需要做到些什么,才能在这样一个隆重场合里站到关键位置?
但是最近这些年,村里已经很少有这样帛布飘飘、哭声阵阵的隆重葬礼了。一切从简。
在如今的城市里,对死亡的处理更是被压缩得尽可能精简。在北京市区,假如一个人在家中去世,家属第一件事是要打电话给120。医护人员上门确认死亡后,很快就需要将遗体运去医院的太平间。
在大城市,遗体一般会在三五天内火化。火化之前,家属可以在殡仪馆举办简单的遗体告别式,那是亲友们最后一次见到逝者的机会。这个遗体告别式,一般就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里通行的“葬礼”。通常很简短,从遗体被推入告别大厅,到送入火化炉,全程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内,大概要完成致辞、献花、鞠躬等步骤。

入殓师旨在让逝者以安详、体面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给予生者慰藉。图为日本电影《入殓师》(2008)剧照
许多人是在不知所措中仓促走完整个过程的。2023年2月,二姐的父亲在北京家中过世。走得不算太突然。2019年第二次突发脑梗之后,她父亲就一直卧床,但真到了那一天,“之前所有的心理建设都不堪一击”。她记得她当时只知道给120打电话,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全是蒙的。”二姐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需要有人一步一步帮她安排后续事宜。
尽管知道花的钱是个不小的数字,二姐仍然对那家殡葬公司心怀感激。殡葬公司让她选个套餐,后续流程逐一推进。二姐只希望能体面地将爸爸送走:老人在家里躺了好几年,最后给他清洁一遍,做一个按摩,能好好化一个妆,让脸色好看一些,穿好寿衣,等等。这是城市里的丧亲者,花钱能买到的基础服务。
但是,很多人在这个流程里受到冲击。西安城郊一位女士的父亲去世后,殡葬公司将遗体运去火化,她看到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打算将遗体装进一只潦草的黑色袋子,“看着像黑色垃圾袋那样的袋子”。还有一位二十出头就失去母亲的年轻女士,发现殡葬公司的人给遗体化妆,“只花了一分钟,而且完全不像妈妈生前的样子”,她接受不了生前那么爱美的妈妈,最后要以这样的面容离开。
对丧亲者来说,殡葬仪式当然是一个表达哀伤、和亲人最后道别的时刻,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在这个紧凑的标准化流程里处理这些细腻的感受。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唐沈琦研究“现代殡葬”,对此的总结是:现代殡葬流程的功能并不在于处理哀伤,而在于“向社会宣告死亡”。

《180天重启计划》剧照
在上海,唐沈琦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一种现象。在某些逝者的追悼会上,首先致辞的不是家人,而是逝者生前的领导。领导表彰确认过逝者曾经的贡献之后,才轮到亲属,有时候甚至没有亲属致辞。“它强调的是公民身份,而不是亲情表达,”唐沈琦说,“殡仪馆要做的事情是如何稳妥地处理好一个公民的死亡,如何安置好遗体,但是处理情绪,他们很可能不会认为这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传统葬礼的抚慰
唐沈琦老家在上海的远郊崇明岛。她见过那种传统的乡村葬礼:一个人去世后,丧礼会持续三天。逝者停灵在家中的厅堂。家人们在村里老人的指导下给逝者擦身、洁面,围着逝者痛哭,夜里轮流守灵。村里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参加丧葬,大家给逝者折纸元宝,聊一聊逝者生前的事情,聚在一起吃流水席。所有人陪伴逝者的最后一程。“整个过程在一种浓郁的亲情氛围下完成,人们没有太多对死亡的恐惧和忌讳,反而能感觉到家庭的力量。”
但放在今天,传统丧仪未必是完美的。研青出生在陕西省中西部的杨陵,这个地方因为隋文帝杨坚的寝陵而得名。在研青出生的村子,一个人去世后,依然允许“土葬”,下葬之前,要停灵七天。下葬后要“做七”,从“头七”到“七七”,都要进行庄重的祭奠活动,家族的同辈亲戚都会到坟上祭拜。随后还有周年祭,直到三周年后,习俗上的悼念流程才会正式结束。
2020年,研青和她弟弟失去了他们的母亲。时隔五年,她还经常回想起那漫长的七天。
第一个感受是疲于应付。停灵那七天,研青每天早上都必须做一碗面放到灵前。可这碗面怎么做,究竟是细面,还是宽面,是煮硬一点,还是煮软一些,已经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于是,每天都有人对这碗面评价指点一番,“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与恶魔有约》剧照
那几天,研青忙得像个陀螺。“家里人来人往,我要给前来吊唁的人端茶倒水,给村里来帮忙的人找烟找酒,安排厨房采购,遣人去购买孝布孝衫……我就像个机器,膝盖已经脱了皮,脑子空荡荡,行尸走肉般活着。”
一些仪式,也让研青感到“水土不服”。比如“哭灵”。停灵七天,亲友来了,第一件事是跪在灵前哭,按照礼俗,研青需要上去安抚。对这一类“号哭”,研青不是很理解——每个人伤心的方式不一样,非得用这种表演式大哭来表达吗?事实上,还有亲戚们指责她为什么不号哭,是不是不爱妈妈。研青盯着棺材角,只想一头撞上去。
但在整个丧仪过程里,也有一些东西触动了研青。首先是亲缘关系。哭丧那天,小姨来了。她是研青妈妈唯一的妹妹。小姨一迈进灵堂就开始唱哭灵歌,一边哭,一边用曲调唱述,讲她姐姐这辈子如何辛苦,如何拉扯大了两个孩子,如何还没来得及过好日子人就先走了。小姨还唱到了她们姐妹年轻时一起学缝纫,孩子们出生后,俩人一起刺绣。研青听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细节,比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小姨会抱着她走很远的山路,上外婆家去。
小姨跪在灵前,哭腔里拖着长音,研青走过去,想将她扶起,但小姨不肯走,拽不动她,研青只好也陪着跪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小姨哭得动情,也许是因为她的唱词勾起了大家回忆的思绪,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她的声音足够大,总之,那个时候,研青陪着跪在灵前,周围的世界离自己远了,她发现自己可以借这个机会尽情地一起哭,没人打扰,也无人劝她节哀。

《承欢记》剧照
晚上,灵堂里照样也是热闹的,灵柩旁边特意支起一张麻将桌,有村里的邻居被邀请留下来打半晚的麻将。给他们端茶倒水之余,研青就跟弟弟到灵堂外面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一坐,聊一聊。聊起妈妈的次数并不多。有时,他们抬头看着漫天星辰,静静地并肩坐着,彼此都没有说话,眼泪无声地流过脸颊。姐弟两个相依在一起,就是一种慰藉。
尽管曾支使得她头昏脑涨,对那些亲戚,研青还是感谢他们在场。母亲的下葬是在上午。研青记得,她从墓地回到家中,突然发现家里完全空了,宾客散去,所有灵堂里布置的东西都被清理烧掉了,中间摆冰棺的位置也只剩下一个台子。一瞬间,她觉得太安静了。她立刻央求姑姑他们别走,再留一晚。研青父亲的兄弟姐妹共五个,当晚大家都没走,他们睡在炕上,研青和弟弟搬了凳子挨着炕坐,听他们聊天。聊的也都不是跟她妈妈相关的话题,但那个晚上,研青觉得挺心安的。
妈妈是意外去世的。当时120的医生来到家里,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跟研青说瞳孔已经散开了,人没了。研青不相信。“明明刚刚掐妈妈人中的时候,她还在喘着粗气,喉咙里还想要发出声音。”她愣在那里,哭不出声,整个人感到十分恍惚。
这种“不相信”,在后续丧葬的一系列流程里逐渐转变为“相信”。妈妈走的那天,赶过来的小姨叫研青快点给妈妈换上寿衣。穿寿衣的时候,妈妈的身体还是软的。遗体在家里要停灵七天。三天后,妈妈的脸色发青,发灰,凹进去了,没有一点光泽。研青心里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寿衣会做得这么肥大,妈妈整个身体都陷在里面,露在外面的脑袋显得格外小。她看一看那张脸,“感觉很陌生。跟心里想着的妈妈很不一样”。
在外省上大学的弟弟直到妈妈去世后第三天,才赶回到村里。到达的时候是晚上,研青领着弟弟来到灵堂,揭开白布,推开冰棺,让弟弟看妈妈最后一眼。研青站在妈妈腰边上的位置,没多想,就伸出手捏了一下妈妈的手,“硬的,而且很冰”。
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些时刻更直观、更具象地展示“死亡是什么”。生与死的界限因为遗体肉眼可见的变化,变得格外清晰。

《婆婆的葬礼》剧照
唐沈琦回想为外公守灵的两个晚上,也有同样的感受。“到第二个晚上,外公的脸颊就瘪了,脸色也越来越灰。虽然我知道那是水分在流失,而且变化很快,眼睛看到了那个‘死’,头脑里就在慢慢接收这个信息。”唐沈琦感到,“守灵”这种形式,对生者来说是很切身的“生命教育”。某种程度上,遗体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让生者了解死亡的意味,“遗体很大程度上还是逝者生前的样子,但又有了不同。躯体还存在,却又变陌生了”。对一个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岁月中漫长的哀伤进程里,首先一步,是要面对和承认“死亡”这个事实。
接着,就是头七、二七、三七、五七、周年、清明、寒衣节的日期,研青觉得,它们就像是一点一点地让活着的人看着逝者慢慢地离开,渐渐地让哀伤一段一段地出走。此后每一次“做七”和周年祭,亲戚们又都会回到村里。研青发现,越到后来,大家的情绪越是轻快起来的。
谈论他们,记住他们
父亲去世几个月后,高古奇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家居品牌"梵几"。当时梵几团队已经有150多人,经营状况也挺不错,周围人都告诉他“可惜”。但他去意已决,创立了“归丛”,要去做殡葬行业。
送别父亲的过程,高古奇有很多不满意。他觉得殡葬用品没有美感,比如,他完全接受不了市面上的骨灰盒,于是自己画图找工厂赶制了一个,赶上了最后的仪式。按照家中长辈要求,他准备了献在墓碑前的塑料花,30块钱一串,“用胶布粘在墓碑上,拆掉的时候全是胶布印子”。两年后母亲去世下葬前,他买了很多纸扎,买的时候反复强调,一定要是纸扎的,人家说没问题都是纸的,都是手工的。结果东西一到,全是化纤用品。这些本来用于寄托哀思的东西呈现得潦草,让高古奇感到痛苦。
葬礼的程序也让他不舒服。高古奇送走父亲的时候,老家当地有个习俗是“摔泥盆”,他需要一边摔泥盆,一边大声喊“爸,跟我走!”。他照做了,但感觉到“很违心”。传统葬礼的很多环节,让他感觉是在“强制表达情感”。另一些环节,虽然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但因为主事者并不了解逝者及其家庭,只是在程序化地执行,一切就变得荒腔走板。高古奇送母亲下葬的时候,仪式上,阴阳师在队伍里说唱他母亲生平,其中赫然有一句话,说老人家“儿女双全”。高古奇觉得很荒谬。他是独子。
现代葬礼到底怎么样才能抚慰人心?高古奇想。传统仪式里的哀伤表达失去了文化土壤,大家不再认可仪式里的某些环节,或许丧葬文化正处在文化转向的路口。现代人需要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告别语法,这并不是坏事,就像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表达过的观点,仪式不是“化石”,而是“流经当下生活的河”。

“归丛告别事务所”将门店设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对面。图为“生命礼仪师”在店里为橱窗模特穿寿衣(李英武 摄)
"归丛"第一次接到葬礼策划求助,是在小红书上。浙江人马先生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突然去世,他找到高古奇,是因为看到他参加一次活动时讲的一句话,"葬礼不应该在人去世几天内仓促完成"。一个丧亲家庭拥有相对充裕的哀伤时长,用这段时间去筹备葬礼,也是种"消耗能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这与研青所在的地区仍然遵循传统守灵七天的抚慰原理是一样的。
一个月后,马先生为父亲办的葬礼在村里的篮球场进行。灵堂里最醒目的是一棵生命之树,高古奇设计这棵树的理念是,每一位来吊唁的来宾都可以为这棵树点亮一盏灯。与此同时,也保留了当地葬礼里的传统,比如“供饭”、锣鼓队,最后的送灵队伍像是《一代宗师》里的场景。
这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葬礼,让马先生很满意。高古奇想,大概也是因为这场葬礼包含了一些必要元素。它有仪式感,“让大家觉得很庄重很庄严,也感觉到美”。它也对逝者生前故事有足够的挖掘。马先生父亲的生平,最后是用“沙画”呈现的,通过两块大屏幕循环播放逝者的故事。马先生对父亲的回忆,从此也走进了其他亲友的记忆中。这是高古奇第一次替别人策划葬礼。他想,假如是放到今天来做,他会花更多时间与更多逝者家属去聊天,去呈现一个更丰满的形象。
谈论他们,记住他们,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一位失去小孩的妈妈总会忍不住跟别人谈起儿子,因为她担心别人会忘了他。一位失去父亲的女儿说,她很庆幸自己不是独生子女,有姐妹一起怀念爸爸,她会觉得“思念的负担小一些”。从个体丧失,到集体纪念,马先生父亲葬礼上的沙画和那棵树,或许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高古奇在模拟灵堂现场,模拟为逝者整理服饰的过程(受访者 供图)
马先生最后的表达让高古奇印象深刻。他在悼词里讲到了很多与父亲相处的细节,比如父亲爱吹牛,比如为了顾及儿子的自尊,把一辈子的存款拿出来,还说这是跟朋友借的,“每次借完钱,我都要写欠条,到现在这些也找不到了”。最后鞠躬前,他说了一句“爸爸,我爱你”。高古奇听到这里掉了眼泪,他当时想,这三个字,他从来没有跟他爸爸说过。
“将和滋养过自己的土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总结出来,把平凡人变身为超级英雄的画面回想起来,把一辈子到嘴边又难以开口的话一口气倾述出来”,高古奇心想,做完这场葬礼,说完这三个字,这位年轻的丧亲者,心里多少能放下一些东西了。
圆满
今年母亲节,研青第一次一个人去了妈妈的墓地。妈妈的墓地在老家以前的芝麻地里。小时候,她总是一手提竹篮,一手提水壶,去芝麻地里给干农活的父母送饭。这里天空蓝得透明,山谷里回荡着一声声鸟叫,周围几乎没有人家,一切都显得寂静空荡。在她拔坟头的草的时候,食指扎进了一根小刺,隐隐作痛;在她流泪的时候,有一只白蝴蝶扑到了她的怀里。她坐在坟头的树荫下,给妈妈讲了很多事情,陪她一起看了她生前拍下的照片、视频,给她放了歌曲《一荤一素》……离开的时候,她在旁边的桑树上摘了桑葚,在山坡上剪了一把野花放在墓前,许愿妈妈会常来梦里看她。
妈妈生前最后一句话,是发给研青爸爸的一条微信,说“你女儿爱吃蘑菇,晚上带点回来”。妈妈去世五年,若说还有什么让研青介怀的,那就是母亲走得太突然,她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和妈妈说。这个遗憾,好像怎么也弥补不了。后来,研青找到一个办法,把这些话发在一个豆瓣小组里。她发现,这个组里的人都在这样做。说一次不够,想念亲人的时候,就再回到帖子里来,继续说。
一场告别,如果想要圆满,并不能光靠完满的葬礼,它需要从死亡降临前就开始。
从EICU担架床上把人推出来的时候,虹雨感觉她父亲是有意识的,因为她问过一句"我们要接你回家,你高不高兴",她记得父亲握了一下她的手,是挺有力的一下。他说不了话,这有力的一下给了她挺多勇气。
虹雨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西安一家医院的EICU住了六七天,医生已经严肃地跟她们四姐妹谈过,意思是老人家的心脏“已经到了烂透了的地步”,而他得的这种病(心肌淀粉样变),所有专家已经无能为力。目前人是昏迷的,靠呼吸机等设备维持生命体征。接下来怎么办?虹雨和她的家人商量了好几天。家里四个姐妹都感觉到,在“是否拔管”这件事上,永远没有正确的决定,但是带父亲回家,可能不会留下遗憾。

《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
她们租了设备,请了护士,又带了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找了一台救护车,将父亲运回了家。护士在她们家里待了三个小时,教虹雨如何使用微量泵、吸痰器,处理留置针。走之前,还帮忙把呼吸机的管子拔了。
嘴巴自由之后,虹雨父亲开始说话,一句接一句,不断地说。不用别人问,他自己就挨个儿地把他记挂的事一件一件说了,叮嘱老伴儿以后不要太劳累。孙辈们也有机会挨个儿上前,他和每个人都握了手。虹雨发现,父亲还是见到小辈们最开心,有时候还会大笑,她能感觉到父亲内心的满足。在这样热闹的情形下离去,这一辈子并没有白活。
突然有个瞬间,父亲张开手臂,拥抱了虹雨,随后又挨个儿拥抱了另外三个女儿。虹雨心想,成年以后从来没有这样跟爸爸拥抱过,“难过又难以忘怀,还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刚摘掉呼吸机后那种亢奋的状态,最终平息下来。虹雨一直没离开过,她看到父亲有时候会抬一下眼睛,偶尔会回应一下,慢慢地就安静下来,好像睡去了。
最后,半梦半醒的时候,虹雨的姐夫妹夫给老人剃了头发,洗了脸,刮了胡子。虹雨四姐妹给他擦了澡。寿衣是好多年前就准备好的。那天,虹雨的妹夫从阁楼上拿了出来,在阳光底下晒了晒,透了透,一共四层13件。父亲没有呼吸之后,姐妹四人一层层给他穿上,男士们也站在边上,偶尔递一下东西,大家的动作都很轻柔。

自从父亲去世,高古奇就开始蓄发(受访者 供图)
高古奇的父亲是2019年去世的。时隔多年,他仍然会感谢父亲,临终时把他叫到床边,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那之前一个多月,他父亲几乎就是半昏睡状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连平时视作掌上明珠的孙女,他都不看一眼。高古奇说父亲那时候“就像是一条老狗”,“要死了,就躲在一个犄角旮旯”。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来了精神,坐了起来,还把高古奇叫到床边,握着儿子的手,要说话。
高古奇脑海里浮现起过去的场景。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那种“社会大哥”,体格高壮,“像个蒙古大汉”。父亲煞气重,通常是让人害怕的,从小到大也几乎很少管他这个儿子,只会非常偶尔,才会当一回“慈父”。但父亲那天说的话,却完全超出他的预期。“他先是说我妈和我,在他人生中太重要了,他说很感激。又说从小没花什么时间和金钱培养我,但是我现在的成就让他挺骄傲的。”

《破·地狱》剧照
随后,父亲又交待了他四件事:一件是关于他脾气太直,容易得罪人;二是叮嘱他不要开车太快;第三件事是关于他妈妈开了那么多年的那个诊所,不要再做了;最后就是关于自己的骨灰,父亲希望将它们撒到他指定的山顶。
当时高古奇就知道,这大概率就是父亲的遗言,为了父亲,他说什么都要去完成。可后来,高古奇意识到,这反而是父亲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父亲给儿子布置了非常明确的任务,当高古奇把这几件事一一完成,他心里有一种充实和圆满的感受。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4期,文中二姐、研青、虹雨均为化名)

排版:小雅/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25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