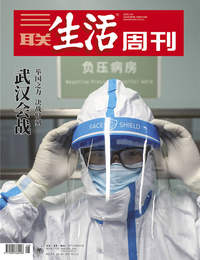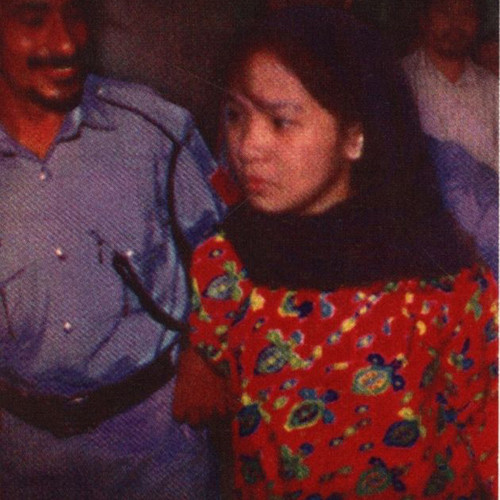歧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20-02-21·阅读时长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221个字,产生2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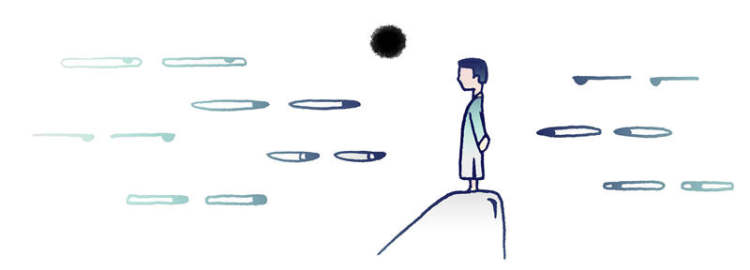
(图 陈曦)
文/何东
昨晚坐Uber去喝酒。司机是个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不想借友邦的幌子转移这段时间的“歧视”,便如实相告。司机连忙问我,是从武汉来的吗?这个信息时代啊,令原来分不清北京和上海的欧洲人,连“WUHAN”这个词都学会了。
我说我刚从柏林来。他反应过来,我德文比他好,应该不会是个从武汉跑出来的旅游者。“我也不信媒体的夸张。”他喃喃自语,“但这种传染病听上去挺可怕的。”我说你别怕,洋葱和羊肉能抵御大部分的传染病。他话题一转,说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视频,中国司机在撞到行人后,不但不报警报医,竟然又倒回车,碾死伤者,为的是逃避高额的医疗费。“这是真的吗?”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实。这种新闻,我自己好像也听过。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巨变时期,总有一些细节被放大,误解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总算到了目的地,我赶紧下车,把土耳其小伙子一肚子的其他问题留在了车上。
歧视是怎么产生的,我后来很长时间在想这个问题。23年前我来德国时,感受到的歧视可能远超现在。在语言班,喀麦隆的同学叫我“嘿,中国”;在大学,老师问我,“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大,为什么你不是‘Schlitzauge’(眯缝眼)”;在聚会上,总被问“你吃狗肉吧?”;在Cyan的工作室,她问我:“中国有平面设计吗?”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维基百科上说,歧视是针对特定族群的,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的特殊性,而非个人特质,遭到不同且较差的对待。但我觉得歧视的根源是不了解。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
发表文章6040篇 获得56个推荐 粉丝47964人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