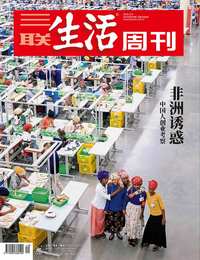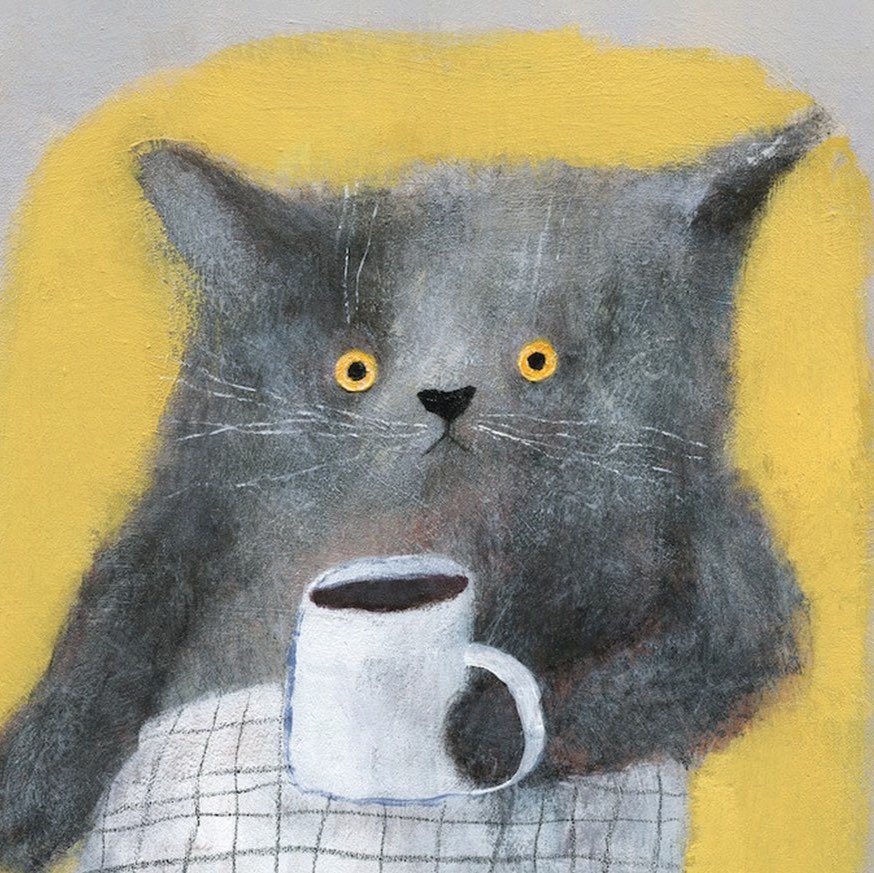厉槟源:在风暴里感受风暴
作者:薛芃
2019-12-09·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124个字,产生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厉槟源青铜雕塑作品《被闪电击中的男孩》
无处不工作室
跟厉槟源的采访约在景山公园,他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2011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住过宋庄、黑桥、京旺家园、草场地几个北漂艺术家的聚居区。草场地的工作室拆迁后,厉槟源由朋友辗转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居所,一个四合院中的两间,朋友给了一个友情价,到现在他住了两年多。
一个从湖南来北京漂泊的艺术家住到了市中心,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应该自得还是自嘲。北京的“一环”内特别清静,尤其到了晚上,从故宫出来的游客散尽,街面上人不多,连个便利店都找不到,他说最好的是不太担心会再被赶走,但心里的漂泊感似乎并没有消散。好在夜晚路边总有些“老北京”扎堆打牌,没事看看还挺有意思。
厉槟源现在是一个职业的行为艺术家,他以此为生,但没有固定收入。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做行为艺术是最冒险的选择,也往往需要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因为行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行为,门槛不高,看起来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艺术家在行为中某些偏执的追求也很难被大众理解和接受,这些作品更是很少会像绘画、雕塑那样,被收藏家买单。艺术家本就是孤独、边缘的群体,做行为艺术的更是边缘。
走进厉槟源的住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堆在外屋,有的立在墙边,有的摊开,里面堆满了日常用品,像是昨天才跟着主人从外地回来。这几年来,随着名气增大,厉槟源外出的工作变多了,他经常出远门,但没有固定的行李箱,看着哪个合适,拎起来就走。他所有的家当里,除了拍摄用的设备,大概就是箱子了。
箱子边上立着一幅大尺寸喷绘照片,其实也是临时的。照片里,厉槟源摆出一副《自由引导人民》中引领自由的“女神”的姿态,画中女子举的是法兰西旗帜,他举的是一盒点燃的烟花,像个即将赴死的英雄。这是2011年在创作《正义》时拍的,那时北京还没有颁布烟花禁令,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开,把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和房屋同时照亮,定格在这个将一切短暂融为一体的瞬间。大相框像个门房似的靠在门口,告诉前来拜访的朋友客人:“这两间出租房,叫做‘厉宅’。”
最近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规范制度越来越严格,厉槟源很少在北京做作品了,因为他的作品太依赖空间与环境,他必须不断向外探索,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是他创作的开始。

艺术家厉槟源
每次去外地,除了参加展览、活动或会友,厉槟源都是带着创作动机去的。他给我看了一件作品《进程》,是去年冬天去鹤岗探好友、演员章宇的班时做的。探班之余,厉槟源也在观察环境,他喜欢把目光投向生态多元的城乡接合部,或者山间郊野,这里有被荒废的人工建筑,也有难得留存的原生自然环境。他把自己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让身体与环境发生某种关联,从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进程》的拍摄地是城郊一片不规则的野湖,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冰面很厚,风也刺骨。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创作计划,四肢绑着四块红砖,从湖面的一端爬向另一端,大约有一公里的距离。这的确是个疯子一般的想法。
但厉槟源不会提前制定好计划,再去找相应匹配的空间,而是让环境去激发自己。每去一个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未知、陌生的,他需要这种新鲜感带来的感官刺激,从而触发出真正的创作动机,也就是所谓的“灵感迸发”。“这种新鲜的感觉是第一经验,如果当下不立刻把想法做出来,再去揣摩几天,感觉一消失,就什么都做不出来了。”厉槟源说道。
厉槟源没有助手,所有行为的实施、拍摄、剪辑都是自己完成。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他必须自己掌控机位,调整拍摄的角度。“找助手太贵了,而且只有我自己知道怎么拍我自己。摄影机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眼睛,我怎么看我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在找到空间、蹦出想法与实施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厉槟源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性格——冲动、偏执、较真、自我,在这种状态下,助手的确无处安放。
文章作者


薛芃
发表文章137篇 获得5个推荐 粉丝920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