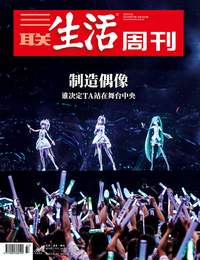再见,凉面
作者:黑麦
2019-09-12·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187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插图 赵阳)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在炎热的夏天做芝麻酱凉面给我吃,她把黄瓜丝、煮黄豆、豇豆丁这些菜码分别放在不同的盘子里,使桌上看起来丰富些,吹着电扇坐在餐桌上等着面出锅、过水的时间,好像总是过得特别慢。这是曾经的北方家庭里最常见的夏日场景。
姥姥家一直住在西单的灵境胡同,她家的凉面从不与芝麻酱为伍,姥姥是老北京人,她喜欢用酱油炒肉丁,关火时再淋上几勺香醋,那黑色液体沾锅的瞬间,立刻激发出一股酸味冲鼻的烟雾,这是我对于醋烹最初的印象。吃凉面时,她会给我拌上香菜,随着醋味的扩散,那种曾经难以下咽的草药味道最终和面麦的淀粉和解了,化为一种爽口的清香。
在北方的餐桌上,凉面被调料划分成两个鲜明的阵营。芝麻酱凉面在夏天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很好奇北方人对于芝麻酱的热爱,这或许和它作为涮羊肉的唯一蘸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毕竟任何食材裹上芝麻酱都会成为一种相似的味道,在热爱涮羊肉的北京,凉面自然也逃不出被麻酱入侵的宿命。其余的凉面需各自为战,用那一丁点酱汁的味道厮守着彼此的态度和地域立场。
好吃的凉面并不少见,南城的牛街一带比比皆是。在老汤拉面馆,牛骨汤拉面在夏季摇身一变,成了新疆风味凉面,碱水硬面就着冰爽的西红柿片,组成一道经典的消暑主食;峨眉酒家的鸡丝凉面容纳了经典的川味,辣椒的混入让面与鸡丝亲切地融为一体,充满嚼劲;当然硬面也有对立面,在著名的林静麻辣烫里,面几乎要被煮坨了,黏黏质地的从面筋中散发出类似“烩”的味道,坨是一种口感,有些人专爱这种柔糯,是因为酱汁被无限地吸附在上面,挥之不去。
凉面和冷面,听起来是亲戚,实为宿敌。延吉、朝鲜和韩国,是多数冷面的故里家园,或黄或灰的荞麦面,倔强地躺在一大碗汤汁里,给人一种温泉泡汤时的惬意感受。它的口味酸甜,接近饮料的冰点,而爽滑的面并非这里的主角,称霸其中的,是辣白菜、牛肉片,甚至是煮鸡蛋和水果片。在望京的三泉冷面馆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气泡冷面,当服务员把冰冻苏打水一样的汤汁倒入碗里时,我几乎认定了这汤才是碗中的领导者。血统纯正的凉面也会过水,古称“冷淘”,这流程不过是为了降低面的温度,顺便洗净面上多余的淀粉味,使其变得紧致、滑口。真正让两种面产生对立的,是餐饮营业者对待这两种面的态度,冷面被认定是四季咸宜的美食,而凉面,只能沦为夏季的时令。
文章作者


黑麦
发表文章231篇 获得12个推荐 粉丝2334人
沉迷于对抗中年危机的美食作家,对groove着迷的音乐编辑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