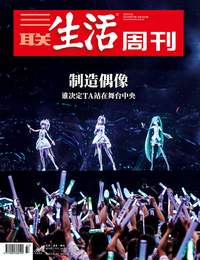重看《革命之路》
作者:驳静
2019-09-12·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689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一个无望的婚姻故事
《革命之路》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城郊。一对青年男女,初见时意气风发,婚后,二人住到郊区,在名为“革命之路”的尽头选中一幢漂亮的小房子。男青年弗兰克以一份“全世界最无聊的工作”养家,而当年那个怀有演员梦的女青年艾普丽尔,成了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太太,两个孩子的母亲。只是,她心里仍有一点不甘平淡的火苗在作祟,直到一天晚上,这点火苗燃烧起来,催生出一个改变——搬去巴黎。“我可以在那里干一份秘书工作,直到你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男青年被说服了,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二人的精神状态,小房子里洋溢着“幸福的癫狂”。
幸福的癫狂,被艾普丽尔再次怀孕的事实打断。反观弗兰克的大松一口气,“一个欢快的笑容挣扎着要爬到脸上”,艾普丽尔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最终选择了流产,她使用了一种现代人看来荒诞的“橡胶吸液器”,并因此出血过多而丧命,癫狂的幸福感最后惨淡收场。
悲剧发生后,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又花了一个章节,专门讲述各色人等在艾普丽尔死后的反应,仿佛这绝望的浓度还不够似的。故事最后一页,那位卖房子给男女青年的吉文斯夫人正与听力障碍的丈夫喋喋不休,诋毁艾普丽尔:“如果有人花了那么多心思给你送来一盆好植物,一盆能蔓延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写到此处,耶茨是这么结尾的:“不过从这里开始,霍华德·吉文斯什么也听不见了。愉悦的、雷鸣般的寂静席卷了他。他关掉了他的助听器。”
如果说目睹艾普丽尔的死令我心头一震,这悲剧后的平缓一章,则令那种绝望感变得密密匝匝,仿佛眼前已经是死寂。耶茨没有救赎他书中的人物,没有给读者留下一点希望的出口,难怪这部小说当时无法获得大众意义上的成功。耶茨的这部长篇处女作出版于1961年,不是畅销书,也未能获得什么奖,因此这样一个无望的婚姻故事,要想流行起来,还得依赖好莱坞的意愿。它的电影改编命运多舛。这个电影项目在多位制片人手里兜兜转转,一直没有下文,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终于被拍出来。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她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于是拿着剧本,先后游说了两个人,一个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二人自成名作《泰坦尼克》之后就再也没合作过,另一个则是门德斯(Sam Mendes),当年曾凭借《美国丽人》惊艳好莱坞的那位导演,也是她(当时的)丈夫、她两个孩子的父亲。
2019年,中国话剧导演姜涛将这个故事搬上戏剧舞台。话剧版《革命之路》的编剧是一对夫妻(朱珠与田晓威),男女主演恰好也是一对夫妻(胡可与沙溢),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台“喜剧”。好的戏剧作品并不拒绝喜剧手法,但当创作者为这样一个绝望的故事设置了过多喜剧梗时,故事中的阴暗色调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台上演员抛出的每一个梗都被观众接到了,以至于,一开始对此深感抵触的我,后来也逐渐地放弃了那点小小的执念。婚姻关系中的那些苦涩,的确会叫观众会心一笑。
死亡发生前,那是艾普丽尔日益绝望的过程。当我重新再看原著,又对比了电影版,我发现门德斯全盘接收了耶茨的绝望,没有用喜剧淡化命运,而是坦诚地铺展了悲剧命运的本质,他的选择更有力量。或许,如果原著不是如此绝望,中国导演的这个话剧剧本将是个比现在更出色的版本。
文章作者


驳静
发表文章215篇 获得9个推荐 粉丝1128人
j'écris, la nuit tombe, et les gens vont dîner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