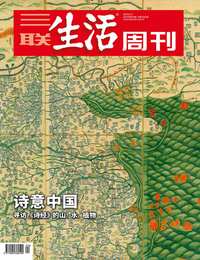沿淇河而行
作者:丘濂
2019-06-12·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081个字,产生4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淇河的许家沟河段有温泉,鸭子吃了水里的矿物质可下“缠丝鸭蛋”(视觉中国供图)
温润年代
前边便是淇河了。
转过一片竹林,空气陡然变得清凉,视野也豁然开朗,让我看清了它的面貌:这是一条从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绿河流。靠近岸边的地方清浅可见碎石,河水的中间则有几块翡翠色,那是深度发生了变化。不远处横亘着几处不到半米的断坡,让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发出了哗哗的声响。《诗经·卫风·氓》中写“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说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湿了车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样子却像是诗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鹤壁市一个叫作竹园的小村。这里也是我踏访淇河的起点。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渐摆脱了太行山脉的束缚,开始进入到平原地带。《诗经》中《邶》《鄘》《卫》三风便发生在地处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区。这座古意盎然的村庄,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间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当地称“九门相照”。即便已经开发旅游,仍有着属于乡村的宁静。“竹园”得名于过去这里广泛生长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诉我,本地优质的竹材还成为了修建紫禁城时的建筑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们想到的多是长江以南连片的竹林,并不觉得它会是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风物。一问果然。此时目之所及,纤细的刚竹都是近两年才栽种起来的,为的就是恢复《诗经》以及历代文学作品在歌咏淇河时,所描绘的样子。
与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咏物的象征。《诗经》中七次咏及竹,《卫风·淇奥》更是对竹子的样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奥”作河水弯曲处来讲。全诗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来起始,表面写的是在淇河拐弯处,竹子郁郁葱葱的状态,实则是以竹子来起兴,讲君子仪态美好,令人难忘。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梅、兰、竹、菊早已不是简单的植物,而是各自对应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为托物言志的象征。以竹子来喻谦谦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这篇《淇奥》。由《左传》中季札观乐时,对于《卫风》的评价可知,《淇奥》是在赞美卫武公的美德。《诗经》研究者李山推测,它属于《卫风》中较早的篇章,时间在两周之交——太戎杀周幽王,卫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为公,卫国因此会流传有颂歌。“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宽兮绰兮,猗重较兮”等诗句则说明,诗篇的写制和配乐,有可能是为卫武公乘车出行而作。

从桑园村俯瞰淇河。淇河是北方难得的一条清水河(视觉中国供图)
相传,卫武公时期,修建了作为皇家园林的淇园,竹子是其中最为主要的植物。南朝人任昉在《述异记》中就说:“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但淇园的位置则争议不下。一种说法是,就在后世修建的武公祠附近。清代尚书杜臻所撰《卫武公祠碑记》中写:“公祠建于淇县西北,山行六七里,峰回路转,若天设地藏之祠。东北岸建有斐亭,为淇园故址。”那里在“文革”时修建夺丰水库已经被淹没,现在只能欣赏到水库形成的平静湖面,偶尔水浅时,还能看见武公祠残余的地基。不过,在淇河文化研究网的创办人姚慧明看来,淇园应当是很大一片面积,占据了淇河流经鹤壁形成的钝角形大弯曲,那也就是《诗经》里所说的淇奥,卫武公祠周边只是淇园的中心位置。他的依据是,《淇县志》里记载,一位明朝的县令曾经把一块写有“淇奥”的石碑立在弯曲处的高村一带。
总之,繁茂的竹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淇河河畔十分动人的景色,直到清代的诗歌中都还能看到淇竹的存在,尽管它的茂盛程度必定大不如从前。它长势的逐渐衰弱,是人为与自然共同造就的结果。姚慧明告诉我,历史上淇河之竹曾遭到多次大规模砍伐。比如在汉武帝时,黄河决口入瓠子河,汉武帝命人伐取淇竹,将它们编成篮筐后装上石子,用来阻塞洪水;汉朝河内太守寇恂也曾伐淇园之竹,造箭百万,支援刘秀北征燕、代;到了北宋,金军占领中原之后,在太行山一带滥伐林木烧炭,就涉及对淇竹的毁坏。
而气候变化是另一重原因——依照气候学家竺可桢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来看,历史上中国气候变化的整体趋势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低;寒冷期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诗经》横跨的时代,正好属于气候的温暖期,虽然西周初年的一两个世纪出现温度下降,但很快就回暖。当时的气温让黄河流域接近温润的亚热带气候,因此竹子广泛分布,后来竹子生长的区域则向南移动了。沿着竹园附近的淇河稍走几步,我就发现,疏于浇水维护的竹林便呈现枯黄打蔫的样子,今天再造的竹林必须靠人工浇灌来维护。
文章作者


丘濂
发表文章128篇 获得22个推荐 粉丝1484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毕业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美食、传统文化和城市话题爱好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