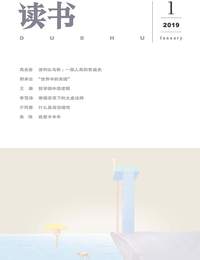评金庸诉江南案
作者:读书
2019-04-11·阅读时长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129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李斯特
“射雕英雄今何在,此间少年已白头。”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着两个月前刚刚一审宣判的金庸诉江南案时,断想不到一周后竟会迎来查先生解脱烦恼的消息。
查良镛(金庸)诉杨治(江南)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于二○一八年八月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主审法院认为:江南的作品《此间的少年》(以下简称《少年》)未侵害原告的著作权,原告主张的角色商业化使用权的著作权保护于法无据,但江南等三名被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在《少年》里,金庸塑造的一众武侠人物化身为汴京大学的学生,演出了一场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青春故事。除人物名称外,《少年》也挪用了原作的部分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这种借用已有作品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再创作的方式,属于当下蔚为大观的同人创作潮流。被称为国内同人创作第一案,本案将对此类创作行为及庞大的同人文化产业产生较大影响,对之深入分析是必要的。简单说,我认为《少年》既未侵犯著作权,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模仿和借鉴历来是文艺创作的不二法门。以金庸武侠论,段誉不能不令人想起贾宝玉;不戒和尚不能不令人想起鲁智深;香香公主战场上倾倒三军,仿佛海伦再站上特洛伊城头;《雪山飞狐》里众口追述胡苗决斗,正似又一出《罗生门》;《连城诀》的狱中传功和杀人梦游砌墙,像极了《基督山伯爵》和《麦克白》。还有《射雕英雄传》与《荒江女侠》的种种对应,《荒江》有九华山论剑、邓氏七怪、丽霞岛,《射雕》有华山论剑、江南七怪、明霞岛,运功逼酒、铁头撞肚皮等桥段如出一辙。金庸自认:“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金庸说他的每部小说都是先确定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配上情节。毋庸讳言,金庸为书中人物所‘配上’的情节,很多都是自大仲马、顾明道等人那里‘借用’的。”(刘国重:《金庸师承考》)仅从文学的角度看,金庸武侠对前人的借鉴,不比《少年》更轻更浅。起大仲马、顾明道于地下,难保不去找金庸讨个说法。这绝不是贬低金庸的创作,因为“优秀的艺术家复制,伟大的艺术家剽窃”,而“唯一区别于模仿的诗人的,是独创的诗人模仿得更深刻些”。夸张一点,几乎所有创作都可视为同人创作—在原有的人物和故事的基础上增添、续写、穿越、混合、变形,以飨同好。正因此,文化私有产权与创作自由永远存在对立。处理同人作品的法律纠纷务必留心两者的平衡,更直白地说,即文化私产强加于社会的成本。本案判决的思路—通过认定《少年》使用的原告作品中的人物名称、简单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以及抽象的故事情节,属于小说类作品的惯常表达,不归《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仅保护独创性表达),且《少年》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发展为全新的校园文学故事,因此与原告作品间不存在实质性相似(即作品的局部和整体均不存在独创性表达的相似),未侵害原告的著作权—是成熟的司法经验的体现。其精髓在于,思想和表达的区分、实质性相似的认定,要服务于促进创作的目标。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72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