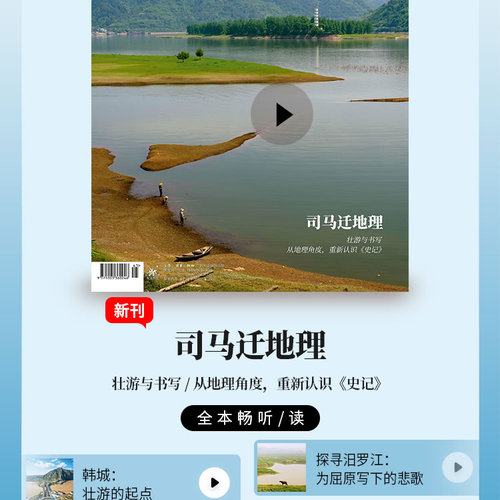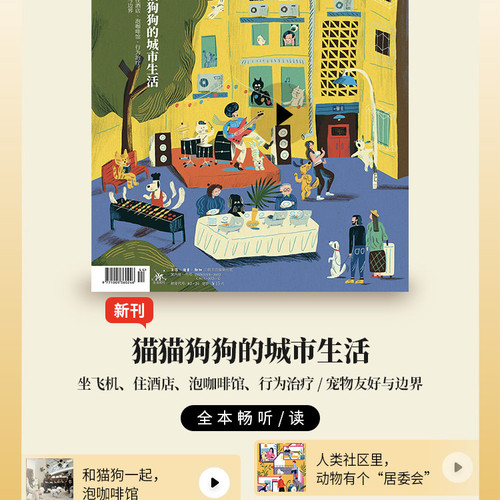张晓刚:记忆只是一个过程
作者:曾焱
2018-09-29·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300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口述/张晓刚 采访、整理/曾焱
这个时代真的是大变了
1978年我20岁,正在云南晋宁县当知青,全国恢复高考后很幸运地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积压了一大批高手,我一个刚入门的艺术青年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在有些惶恐,常常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大二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同学就画出了“伤痕艺术”,然后“乡土写实”,当时好轰动。罗中立的《父亲》是那个节点的高峰。那时期中国美术界诞生了一批明星,也就是我们班上的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等这一拨人。
我那会儿年龄比他们小,身份和心态都是学生。我只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大变了。我碰到了中国美术的历史节点,遇上了在节点最核心的人。这么近距离去感受艺术的变革,我觉得是老天给我机会。
我现在还记得罗中立想起来怎么画《父亲》的情景,因为刚好发生在我们宿舍。有天他过来串宿舍玩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张照片,是黄颜色的背景前面有个黑人。这个调子很明朗,很强烈。他马上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就是要这感觉。
我们再看见的时候,《父亲》已经完成了。同学们都跑去参观,我只记得感觉很震撼。在当时来讲,一个两米的头像很大了,只有领袖像才能这么大。而且,他画出了皮肤、毛发的质感,画出了那种苦涩的味道。过后就听说这幅画开始展览、得奖、发表……当时大家都是同学嘛,关系太近了,也没觉得他们是大艺术家了那种。但我们班是真的很厉害,隔几天就有一个人出名。几天不见面,见了问:“你最近在干什么?”“我在画画,等画完了给你看。”等到画完一看,哇,就吃一惊。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进入创作状态了,可我还在拼命学习,怎么画素描,怎么画色彩。直到四年级,我才开始真正去想艺术的问题:我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我那时喜欢西方现代艺术,决心做一个像凡·高那样的现代主义画家。
1982年我毕业回到昆明,找不到接收单位,去集体制的玻璃厂做过临时建筑工人,几经曲折被招进市歌舞团做美工。那年头喜欢现代艺术意味着你彻底的边缘化,我和好友毛旭辉、潘德海等相互支撑,一起看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哲学和文学,也常常一起喝大酒,相依为命地死熬,之后终于有机会去上海、南京自费办了取名为“新具象”的展览,接着又拉上叶永青等人结成“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八五新潮”时期最早的艺术群体之一。从中国美术史来讲,“八五新潮”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它在新时期的中国艺术从乡土现实主义背景上深化和转向至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形式探索和思想观念方面具有革命性。我觉得要说很有个人价值的作品,可能并不一定多,但它像一股洪流席卷了全国各地,整个时代感觉沸腾了,装神弄鬼的也有,真才实学的也有,鱼龙混杂。
那个时代让人很兴奋,但对刚刚成功的乡土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变化太快了。《世界美术》《江苏画刊》《美术月刊》,国内不多几本美术刊物都在讲现代主义,发展到1987、1988年那会儿,就感觉不是某些人在乱搞了,而是真的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反而原来在主流里边的艺术家开始有了危机感。那个时代很有意思:一边是功成名就的乡土艺术,占据着各种优越的创作条件、展览机制包括市场利益等。另一边呢,我们这帮人又穷又脏又不讲规则,但好像又总在折腾一些什么事。我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年轻人,但已经可以不用按照以往的模式去发展,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大家庭”:怎么去表达中国
第一次通过画廊卖画,是1992年。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来找到我,当时他要和栗宪庭(注:当代艺术评论家、著名策展人)在香港办“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览,计划先把作品买下来。这在当时美术界是件很大的事,因为大家都很穷,有人先买画再办展览,等于是学术、经济双丰收。我把所有作品都摆出来给他,他选了大概几十张。也没有给钱,我们也放心。不放心怎么办?没有其他机会。
1990年前后,艺术圈的人其实都在往国外走。我也想出去看看,但一直到1992年6月才等来机会:德国卡塞尔大学的莱勒·卡尔哈尔德教授以个人身份邀请我去做3个月学术访问。
当时中国跟国外的差距非常大。中国连超市都没有,到外面却天天看见那么丰富的物质、文化,看都看不完的展览,那个刺激太大。那3个月里,我觉得我每天都没浪费,有机会就背着水和面包关进博物馆,待一天再出来。在中国,人家说我是前卫艺术家,但到了德国以后,人家所谓的前卫艺术我根本看不懂。我能看懂的艺术都在美术馆里,那是我最熟悉的知识结构,80年代再往后我就不甚了解了,等于说我的知识结构落后了20年。
出国很不容易,每个人都会抱着“如果不回来就转换一下身份”的想法。3个月到期了以后,教授问我,怎么样?我说,收获很大。想不想留下来?我说我时间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坚定我一定要回去。这种话说出来好像爱国主义一样,其实我是对自己开始有了很清楚的认知。像徐冰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留在美国了。记得后来1996年我第一次去纽约,当时有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聚会,我碰到徐冰。还是他告诉我,有一本算是国外很重要的《亚太艺术》的刊物,用了我的画做封面。当时他就把自己那本送给了我。
从德国回来以后我一年没法画画,陷入从未有过的迷茫期。我感觉国内变化很大,流行文化进来了,大家都热衷于调侃和谈钱,短短几个月整个环境都变掉了。记得回国后去参加广州双年展,见到国内的朋友,第一句话都是问我,你签约了吗?然后就是请我去很贵的地方下馆子。当时下馆子是件隆重的事情,一般要请很重要的人才咬咬牙把存款弄点出来下馆子。但我回来后发现周围好多朋友都可以很随意了。他们签的台湾画廊每个月会付几千块钱,当时我的工资才200块钱。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所有关于灵魂的探讨,关于价值和追求,最后好像都变成一件商品在货架上出售。我对这种感觉有点悲哀,但是也没办法。拿到钱还是很高兴,是吧?
那会儿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该怎么办,我还要不要做艺术家?远走欧洲的3个月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切。我决定放弃曾经那么喜爱的西方现代艺术传统,我开始想怎么去表达中国,建立自己的艺术体系。
这个语言转换是艰苦的过程。我做了很多肖像画实验,直到1993年夏天,回到昆明家里,偶然翻看到父母的老照片。我无法说清楚那些被照相馆精心修饰过的照片究竟触动了自己心里的哪一根神经,总之难以释手。我画了第一张脸,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我把自己熟悉和习惯的东西一点一点去掉,写实的技法,表现主义的技法,深度、色彩、笔触,能去掉的全都去掉。我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第一个看到“这张脸”的应该是画家陈卫闽,我们共用一个画室。那时候在川美我们是四个人一个画室,中间用隔板隔开。我跟陈卫闽关系比较好,每天都要讨论。还记得是我刚画出第一张三个人“全家福”的时候,他进来了,然后在那儿发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画太好了。我说,是吗?我在画一种陌生的东西。
画了几张以后,我把照片寄给张颂仁。他说,这个是他看过的我最好的作品。1994年画到第六张的时候,张颂仁突然告诉我,说你的作品入选22届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了。同时邀请的中国艺术家还有王广义、方力钧、刘炜等五人。又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但这一次我没问“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觉得自己确实在绘画中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那年正好女儿出生,我没有飞去圣保罗。张颂仁回来跟我说,成功了,说我得了一个铜奖。那年是我的本命年,36岁。之后又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悉尼三年展等等,开始忙起来了。
文章作者


曾焱
发表文章58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2128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