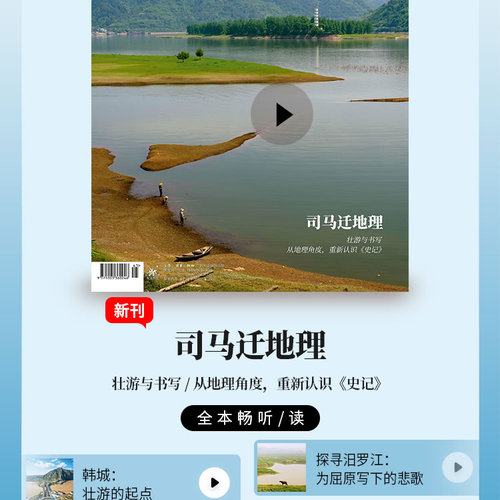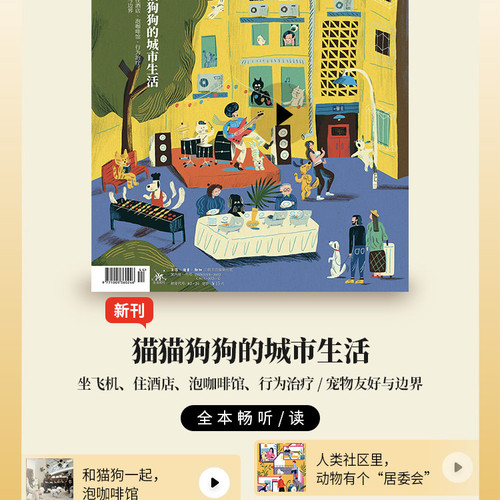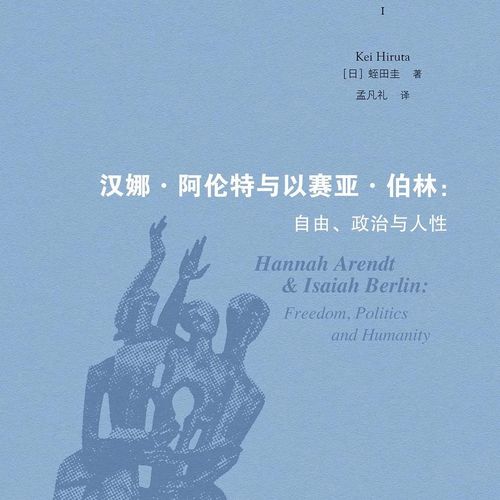徐冰:我为什么会做出“英文方块字”?
作者:曾焱
2018-09-29·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594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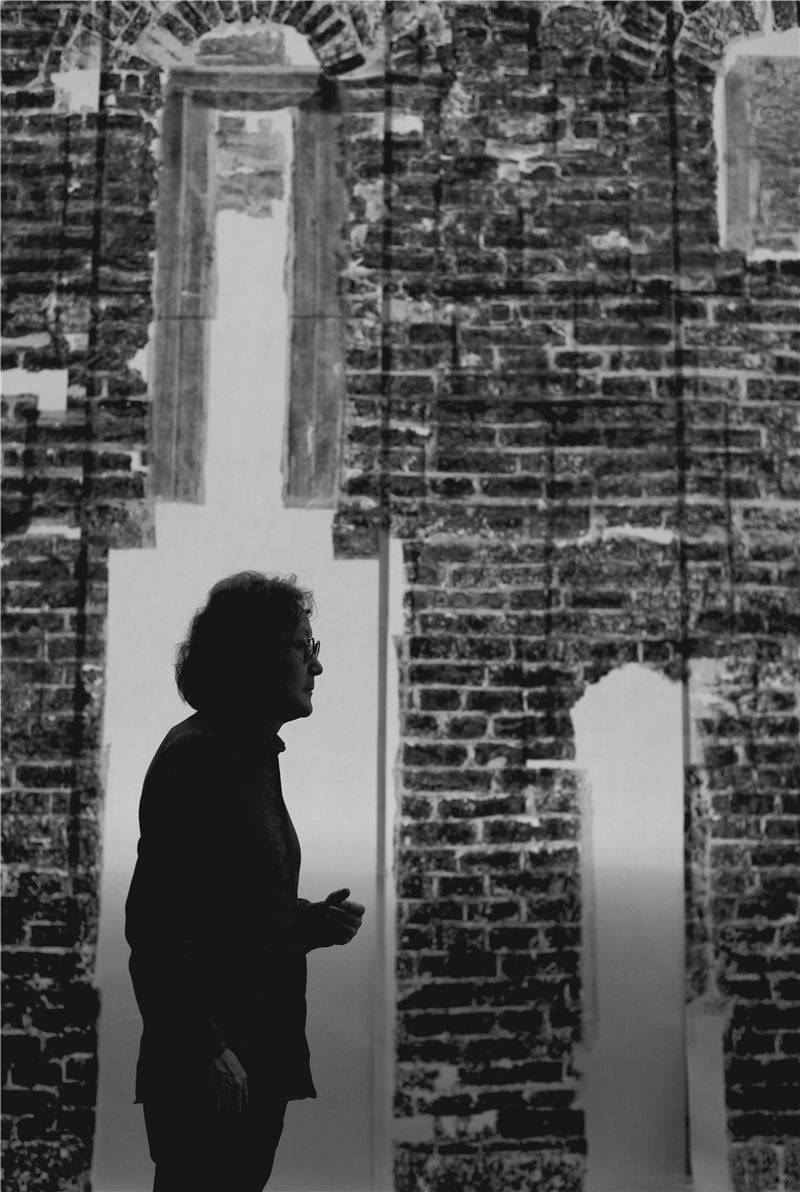
口述/徐冰 采访、整理/曾焱
我是1990年去的美国,随身带着《天书》《鬼打墙》的资料和两卷《五个复数系列》。当时外语不行,到那就感觉有点像一个文盲:你的思维其实很成熟了,但是你的表述能力又跟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冲突给我感受挺深的,也影响了我之后的创作。
第一站去的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Wisconsin-Madison),身份是所谓“荣誉艺术家”(Honorary Fellow)。那时我对当代艺术当然是崇拜的了,就一心想做和他们能接轨的东西。很快我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个人展览的机会,在美国博物馆做了第一个展览。我体会到了当代艺术系统的运作,还有作为艺术家在那儿的一种“特权”:博物馆把钱找好,请你去办展,画册、布展、媒体……这些部门都为你一个人服务,最后展览请柬设计完了,还要拿到附近的社区去给居民看,说你们喜欢不喜欢,文字看不看得懂,特别专业化。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艺术家跟在中国不太一样。
90年还有件事对我是重要的,就是我去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了一个题为“高与低”(High&Low)的展览,策展人把一些重要的大师的经典作品和大量通俗的社会资料放在一起对照,揭示那些大师作品思想的来源。我从这个展览开始意识到,当代艺术有它虚伪的一面,对这个系统的弊病有了警惕。
1993年我迁居到纽约。那时候,美国经济开始萧条,他们艺术市场比较好的阶段正在结束,开始进入了低潮。艺术上的动态就是多元文化兴起,艺术家的文化和种族的背景成为主题,全球都一样。在法国有一个重要展览叫“大地魔术师”;后来,又有一个美国的策展人丹·卡麦隆(Dan Cameron)在西班牙做了“生与熟”,也是继“大地魔术师”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展览,主张来自世界各地的在不同文化关系中的艺术家都参与进来。他来邀请我,说得特别兴奋,因为是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美术馆。但当时我没什么反应,因为我根本搞不清西方美术馆系统里的讲究,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之类的。
当时就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和西方近距离接触之初的一种陌生。还记得我和丹·卡麦隆是在纽约东村一个意大利的小点心店里聊展览,一个老头进来,后边跟一个年轻人,他就压低声说,这是金斯堡(注:美国“垮掉一代”著名诗人)。当时东村就这种感觉。
那时特别忙,因为多元文化了嘛,跑到世界各地创作和展览,全是我们这种具有边缘文化背景又生活在欧美中心城市的所谓多重身份的艺术家,带着各自独有的背景成分,做着最极端、最具实验性的艺术。走到哪儿做展览差不多都是一批熟悉的脸。中国艺术家在纽约的,主要是我和蔡国强比较活跃。欧洲有黄永砯、陈箴。这种全世界跑来跑去的经历,差不多延续到了2000年。那个时期我对国内当代艺术已经没有特别的关注,说了解也就是政治波普什么的,看过一些作品,印象还挺深的。
我当然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融入国际,但我后来认识到,其实你的东西是不是在那生效,在于你能不能通过你的艺术,把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优质的部分给呈现出来,从而对那个系统中盲点的部分有调节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那里不需要再多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东西。这是后来才悟到的。
我是说过,1993到2000年之间,“中国的新潮艺术越发成为小圈子和迎合西方策展人的活动”这种评价。我自己在那个时期有没有这种心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和直接的迎合又不是一回事。
我在美国时期的作品,很多都带有比较强的中国的思维和中国的方法。那会儿老有人批判中国元素什么的,问题是,我一直就相信艺术家身上携带的东西与作品结果有直接关系。比如说1987年我做《天书》的时候,就想做当代艺术,但是做出来以后却是里里外外的中国的方法和中国的材料。那时候我跟西方没关系,也谈不到迎合西方,可要从后来效果看,感觉它是我最“迎合”西方的一个作品,因为使用了很多中国元素。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携带了你特殊文化基因的这一类作品,在一种全球的多元文化的浪潮中,可能更容易被关注和接纳,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
文章作者


曾焱
发表文章58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128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