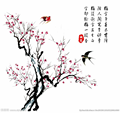海子抒情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共时性
作者:萧飒
2017-10-07·阅读时长18分钟
摘 要:海子作为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抒情诗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本文主要从T.S.艾略特的“共时性”角度出发,从意象、语言、音乐性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海子抒情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审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海子,抒情诗,古典诗歌传统,共时性
绪论
二十多年过去了,海子在中国新诗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加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他的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微妙。从一开始,由于时代氛围,文学生态、批评取向以及有意无意的“误读”等诸多方面原因,海子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从朱大可先生的《先知之门》起直到现在,我们谈论海子,仍旧主要把他置于西方形而上学背景下,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范畴内。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当然与海子本人脱不了关系。海子无论是在作品还是在文论中都大量显示了自己与西方诗歌的密切关系,而对中国古典诗歌论述较少,而且多含贬斥意味,这就使得我们在谈论他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事实上,一位诗人不论怎样承认受外来影响,也不管他对本国诗歌传统态度如何,他与古典传统之间总处于一种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正是他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海子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用汉语写作,如果他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尚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我们很难说他的地位是绝对稳固的。
从纯粹的诗歌角度,在中国新诗史上再难找出一位诗人像海子一样同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复杂且意义重大了。对于这一点并非没人意识到,在海子逝世不久后,诗人陈东东就曾说过:“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1】可惜陈东东对于海子是如何影响过去这一点未加详细阐述。对于考察一位诗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论述对于我们依旧有重要启示:“……历史意识有含有一种顿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2】艾略特这段话虽是在论述诗人的创作,但如果我们在批评中也能这样一种“历史意识”,能够深刻理解个人与传统的“共时存在”,许多晦暗、复杂的关系就会变得明了清晰。
本文的论述集中于海子的抒情短诗,除了笔者自身的能力与认识的局限之外,其余的两个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海子的抒情诗的成就已被公认,而他的长诗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第二,就古典诗歌来说,抒情短诗占据绝对主流(真正意义上的长诗怕只有屈原的《离骚》了)。海子长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更为曲折、隐蔽,其间的障碍不是笔者当前所能克服的,只有更俟他日了。
一
“这一次全然涉于西方的诗歌王国。因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①在海子为数不多的几处对古典诗歌的论述中,这一处要算最为著名的了,我们要论述他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自然也离不开它。整个古典诗歌历时两千余年,其间流派众多,学说纷纭,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了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海子这句话确实击中了古典诗歌的一个要害:趣味一直在古典诗歌中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尽管在不同时代它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由于海子对于诗歌中趣味的蔑视,使得他对尚未沾染文人趣味的《诗经》的重视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这一点燎原先生在《海子评传》中有独到的论述:“而由这一文化/文学空间贯注给海子最杰出的成果,便是与《诗经》相贯通的麦地、农耕题旨的抒情短诗。‘翻动《诗经》/我的手指如刀/一下一下/砍伤我自己’这是海子再长诗《但是水、水》的标题记。他以这样一种“被砍伤”的极端表述,言说《诗经》之于他的刻骨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经》确立了海子,它是海子藉此而对诗坛那一强大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主流说“不”,也是由此对自己说“是”并大地独步的凭借和转折点。”【3】
《诗经》作为整个古典诗歌的起源,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代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为后世古典诗歌确立了最基本的抒情手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赋、比、兴”。《中国文学史》对这三者的解释是:“赋,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有关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的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4】在后世古典诗歌中要想找出一首没有用到这三种手法的诗是极其困难的(或许只有李白、韩愈的某些诗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例外)。但在海子的诗中我们找不到,梁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很有见地的写道:“相对赋比兴手法,海子的诗又是对几千年不变的抒情语体模式的冲击和变革。……海子的诗则完全摆脱了赋比兴结构的模式要求。他不经过叙事,直接进入抒情,在每一个独立性的抒情句式之间,造成遥相呼应的意象联系,搭起空间结构的框架,让读者的想象力参与漫游,有更多的鉴赏和旋转余地。抒情诗空间信息结构中“场效应”的形成,给语言方式带来多元开放、组合变化的可能性。”【5】后世诗人及诗论家正是在“赋比兴”的基础上演化出各种各样的诗歌理论:如荀子《乐论》中的“物感说”、钟嵘的“滋味说”、陈子昂的“兴寄说”,严羽的“趣味说”……以及清末王国维集古典诗歌理论之大成的“境界说”。这些理论看似纷繁,其实还是有一个内在核心作为基础的:那便是作者的主观情感(情)与客观事物(景)之间的关系。情与景的交融程度一直以来都被当做评判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而这,恰恰就是海子所贬斥的“文人趣味”。
对古典传统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之后,我们必然会面临这样两个问题:海子在自己的诗中是怎样摒弃自己所贬斥的“文人趣味”的呢?作为整个古典诗歌源头的《诗经》又是如何确立海子的呢?我们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我们可以先从第二个问题入手。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诗歌总集,不管它是成自于“采诗说”、“删诗说”,还是“献诗说”,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它里边的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诗篇,是来自于劳动人民中间的。它所描绘的世界同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劳作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性。《诗经》中出现的意象,直接来自于作者们“生于斯,劳作于斯,死于斯”的大地。同劳动人民本身有着一种深刻的同源性,正是这种同源性,使得那些意向尚未真正成为坐着们刻意的审美观照对象,而保持着无比鲜活的源初的朴素性。随着古典诗歌文人化的程序一步步提高,辞藻固然日益丰美,内容日益扩充,情感日益复杂,修辞日益精巧,但他们所描绘的意象也越来越成为其赏玩的对象,成为其承载情感的工具,而丧失了《诗经》中的朴素性。
在笔者看来,《诗经》根本上确立海子并非在题旨上(麦地、农耕题旨),而是那种源初的朴素性,这也成为《诗经》以后的整个古典主义的分野。
二
“荷尔德林的诗,是真实的,自然的,正在生长的,像一棵树在四周的山上开满了杜鹃,诗和开花,风吹过来,火向上升起一样。”【6】这是对他最喜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描述,事实上把这段话看作海子自己的诗的写照也同样贴切。它生动地说明了海子诗中的那种朴素性。笔者认为,贯穿于海子抒情诗中的朴素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意象层面和语言层面。这两个面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在意象这个选取上,海子的诗同《诗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也是主要选取了同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景物:麦子、麦地、村庄、粮食、泥土,河流、月亮、少女……但二者在对待各自景物的态度上有重大的差别,在《诗经》中,物的出现多半不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而作为一种“赋比兴”的抒情手段,引出抒情对象;而在海子的诗中,物具有独立的言说功能。在这一点上海子的诗与《诗经》之后的古典诗歌的区别也是极为明显的:在古典诗中,物是作者投射主观情感的对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的一句话可以极好地概括它们的功能:“一切景语皆情语。”【7】他们写的月亮是“我寄愁心于明月,随君知道夜郎西”,写落花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写春风的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山峰是“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在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的并非物的本身,而是作者的主体情态。一句话:在古典诗歌中,物处于一种被主体情态遮蔽的状态。而在海子的诗中,麦子就是麦子,村庄就是村庄,月亮就是月亮,这些意象当然也承载着意蕴,但并非作者的私人情感,而是物自身的呈现。我们所感受到的是物自身的言说,而非作者的主观趣味,但这不意味着海子的诗就摆脱了主观性。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有这样一段话:……您把主观性赶走,它又飞快地跑回来。当然,当它回来时,似乎有所不同了。流放和否定具有一种净化价值。主观性在不在场之后重新出现,他/她摆脱了那些肤浅的品质,它的伤感,它的过分的个性,以及那些似乎使它在作品之外与某种人类的存在,是种传统的真实相联系的虚幻的关联。”【8】为对这段话有更好的理解,我们来看下面的诗句: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一层层白云覆盖着
我
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地
------ 《活在珍贵的人间》
雨水中出现了平原上的麦子
这些雨水中的景色有些陌生
天已黑了,下着雨
我坐在水面上给你写信
-----------《遥远的路程》
这些诗中也有一个“我”在,但在“我”出现之前,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自我“流放”和“否定”的过程。在“我”再度归来之后,显现出的是一种深刻的哀愁和无畏的坦然,就是在最优秀的古典诗中,这中“流放”和“否定”,也是察觉不到的。正是海子的这种痛苦的自我流放与否定,扫除了几千年来蒙蔽在“物”身上肤浅的情感与趣味的尘土,使我们贴近了物本身,从而达到生命本身的关注。“有两类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与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的大生命的呼吸。”【9】毫无疑问,海子属于第二类诗人。
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海子抒情诗的语言:
故乡的星和羊群
像一支支白色美丽的流水
跑过
小鹿跑过
夜晚的目光紧紧追着
-------《我们及其他的见证人》
村庄里住着
母亲和儿子
儿子静静的长大
母亲静静的注视
芦花丛中
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
我的妹妹叫芦花
我的妹妹很美丽
------《村庄》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乳房也美
水很美,水啊
无人和你
说话的时候很美
--------------《给母亲(组诗)》
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些语言简到极致的诗时,总能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的震撼。我们被击中了,但又说不出是哪儿。此时似乎一切已有的诗歌理论都失效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中蕴含着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应该说这是他自觉的追求,他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对于表象和修辞的热爱,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描绘-----这样一些疾病的爱好。”【10】
任何语言在诞生之初并被使用起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语言在不断重复使用中被磨损、蒙上灰尘,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化而丧失最初的灵光。诗歌作为一种审美语言尤其如此。为了弥补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借助于修辞。随着诗歌的发展,修辞技巧日益繁复高超,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诗歌源流不断的国度修辞技巧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修辞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能指和所指相互偏离的一个过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11】由此古典诗歌越来越偏离《诗经》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卫风·燕燕》”中的朴素状态。这是诗歌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谁要想溯流而上,谁就得冒着“尸骨难收”的风险。然而海子就这样做了,而且做的如此彻底。他这种貌似顽童不经意间推开神秘的门的举动的背后需要超人的胆识和勇气:“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祖国(或以梦为马)》”事实上证明,他成功了(虽然不是全部),这不能不说是新诗史上最大的奇迹之一。
在下面这首《月光》中,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好!
照着月光
饮水和盐的马
和声音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美丽
羊群中 生命和死亡宁静的声音
我在倾听!
这是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谣 月光!
不要说 你是灯中之灯 月光!
不要说心中有一个地方
那是我一直不敢梦见的地方
不要问 桃子对桃花的珍藏
不要问 打麦大地 处女 桂花和村镇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好!
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
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
月光照着月光 月光普照
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
-----《月光》
“月亮也是古诗中/一座旧矿山《哑脊背》”,在古典诗歌中再没有一个意象像月亮一样受到诗人们如此多的青睐了,从《诗经》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到《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光似霰”到王维《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到东坡《永遇乐》中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到美成《解花语》中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月亮成了诗人展现其才华的最佳舞台。为了将月亮描绘的独特出众,诗人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在《月光》的开头,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今夜美丽的月光,你看多好!”
这可能是新诗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开头了。它如此简单,甚至连白描都算不上。仿佛以前从未有人写过月光,其中包含着初次发现的无限喜悦。这句诗有两个修饰词:美丽和好。这是两个最最空泛的形容词,一般诗人都避免将他它们入诗。海子却把它们用在了一起,并且是在一首诗的开头,这两个词构成了一扇门,一扇通往古典主义的门(但它们本身并非古典主义)。这个开头以同一个句式在诗中重复了三次(其中有两次是一模一样的),这就使得古典诗歌中的月光构成了我们读这首诗时的一个共时语境,二者形成的一种互文关系。正是这种共时语境,这种互文关系,才是《月光》无限魅力的真正来源。
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读着海子那些看似简单的诗句时,同时也在读着整个古典诗歌传统。
四
或许我们在读海子的诗是,感受到它们与古典诗歌联系最为密切的不在于意象和语言,而在于音乐性。这样的诗句在海子的诗中随处可见:
我请求熄灭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我请求下雨
我请求
在夜里死去
-----《我请求:雨》
鸟 在家乡如一只蓝色的手或者子宫
手和子宫
你从石头死寂中茫然无知的上升
-------《在家乡》
我们知道,诗歌在诞生之初就与音乐密不可分。中国最初的诗歌就是“诗乐舞”一体的。《诗经》中的诗篇是人们在劳作、祭祀或者宴会上歌唱的。当诗歌转向文人创作后,这种歌唱功能渐渐消失了,但其音乐形式保存了下来,并且日益完善精细。从《诗经》到律诗的定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诗歌(不论是诗、词还是曲)的音乐性一旦成熟完善,便不可避免的走向僵化。这除了文学发展自身的“惰性”之外,和汉语自身的特性也有关。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有响亮的韵腹,还分平、上、去、入四声,它本身就带有极强的音乐性。这对于诗歌创作固然有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种妨碍,它缺少那些以呼吸节奏、重音以及长短不齐的音节为主的音乐性的语言(如拉丁语系的语言)所具有的含混、变化与自由。因此,海子把汉语称作:“汉族铁匠打出的铁轨中装满不能呼喊的语言。《太阳·弥赛亚(原始史诗片段)》”
古典诗歌中的音乐性明显不能满足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的需要了。白话新诗中,对待古典诗中的音乐性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未加实质性改造的移植。这主要以现代诗中的新格律派为代表(如新月派,以及朦胧诗中的某些诗歌);二,完全抛弃,这主要以后新诗潮中某些具有“反诗”倾向的诗人为代表;第三种算是一种折中方案,以一种智性、审慎而含混的“语调”来作为替代。这主要以受西方现代诗影响的学院派诗人为代表。第三种情况应该是当代诗歌的主流,但是这种“音乐性”如此含混、隐晦,以致于有时让人感到近乎脱离汉语自身的特性。
区别于以上几种情况,海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咏唱。他在《日记》中说:“但是旧语言旧诗歌中平滑起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尸体是不能出土的,问题在于坟墓上的花枝与青草。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和咏唱的合一。意象的平民必须攀上咏唱的贵族……【1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子对于古典音乐性的态度:对于“不加实质性改造的一移植”和“彻底的抛弃”都是不赞成的,而“用智性、审慎、含混的语调作为替代”显然不能满足他“意象和咏唱合一”的要求。他的“咏唱”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一次古老的回归(甚至跨越了古典主义),回到诗歌最初的功能上:歌唱。这又是一种全新的歌唱,因为它建立在全新的语言和音乐形式之上的。在这之中我们能清楚的感受到他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自由体颂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完全根植于汉语自身的韵律与节奏之上的。这正是他超出其同代诗人的地方。他的诗,既摆脱了古典诗歌中那种刻板、僵化、表面的音乐性,又没有陷入学院派诗人“语调”的泥淖中,而成为种真正自由的咏唱。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
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村庄》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只为她们破碎
-----《四姐妹》
泉水白白流淌
花朵为谁开放
永远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
吐着芬芳,站在山岗上
--------《四姐妹》
在这些诗句中,音乐来自于一种歌唱的直觉本能,而非智性的安排。《月光》这首诗是海子咏唱的典范性作品(引诗见前文)。歌唱像水一样了无痕迹又无处不在,像呼吸一样自然,渗透到每一个词语与意象中,超越了形式与技巧,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在诗歌中达到一种本体的地位。在这首诗中海子真正做到了“意象与咏唱的合一”,我们分不清是人在歌唱还是月光本身在歌唱。歌唱带来一种醉,并非古典诗歌中的自我陶醉,而是生命本身的沉醉。
和古典诗歌依托的宁静田园世界不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复杂、混乱、无序、漂浮不定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歌唱是一种理想,它保存了我们对一个更源初世界的记忆。在海子那些最优秀的抒情诗中,世界被纯化了,一种自由的秩序再一次被建立起来。
结语
自五四新诗运动以来,汉语诗与传统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难以回避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当前汉语诗发展的困境与这个鸿沟不无关系。我们需要重新架起通往过去的桥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海子在新诗史上的独特地位凸显出来。本文正是想通过对海子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共时性的研究而达到这个目的,也希望能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有所裨益。然而,海子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课题,由于文章篇幅以及研究尚未深入的原因,本文只是选取了几个笔者认为主要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并未充分的论述,其中不乏片面主观的见解。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行对这个课题进行更加客观、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骆一禾.海子生涯[M]//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2] 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
[3] 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3
[4]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二版)[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5] 梁云.海子抒情诗风格论谈[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5)
[6] 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M]//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7] 王国维.人间词话[M]郑晓军,编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9] 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M]//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10] 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M]//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11] 王国维.人间词话[M]
[12] [10] 海子.日记[M]//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① 本文引用的海子的全部作品都来自西川编的《海子诗全集》
文章作者

萧飒
发表文章48篇 获得8个推荐 粉丝80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