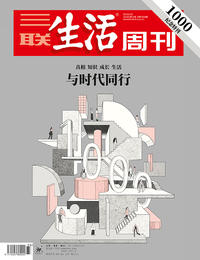答案在最后一公里
作者:刘怡
2018-08-16·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968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地图里的世界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的书架顶端常年摞着两本地图册:一本是简装的《世界地图集》(地形版),另一本是已故历史学大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主编的第二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它们都不属于漂亮的精装版,并无收藏价值,许多页面已经留下了铅笔画出的记号以及手指翻动造成的污损痕迹。尽管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打开“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软件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关于陌生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有效信息,但在闲暇时光里,我依然乐于像过去十几年一样,带着纯粹的好奇心翻阅这两本旧地图册。
《世界地图集》展示的是一幅静态而充满障碍的空间图像:自人类文明起源以来,山川河流、江海湖泊等天然地理常量已经很少再发生频繁或剧烈的变化。它们的存在方式与复杂程度,对各共同体之间的资源、权势分布以及制定和实行相应的对外战略形成了一种天然制约,并且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段内造成持续影响。《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则呈现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动态变化: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塑造和开发地理常量“可用潜力”的能力始终在获得有效提升:天堑可以成为通途,荒漠里也许能发现石油。这种因开发而导致的互动和碰撞,催生出有形的国界和无形的权势政治格局,最终形成了那个存在于观念中的当下世界。
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国际政治学的观察和研究,本质上正是一门“制图学”。那些被称之为“范式”或“模型”的理论工具,提供的正是和地图图例类似的帮助。人们首先决定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根据地形特征的差异,选择一条相对直接或便利的交通线路以抵达那里。但不同于自然地理维度的恒常与笃定,一幅由观念和方法论构成的“地图”往往会被笼罩在形形色色的偏见迷雾之下:一份详尽描绘有各种“机场”“码头”以及“潮汐涨落周期”标识的小比例尺地图,可能会对一个仅仅希望沿着“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的旅行者产生困扰,使其难以分辨信息的实用程度以及目的地的最终方向。但一份仅仅标注有单条“公路”轨迹的极简版大比例尺地图,又可能使旅行者陷入缺乏变通余地的困境:一旦这条“公路”堵塞,他将无法制订任何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最终折戟于半途。
我最终选择了通过对军事和政治冲突的观察,来建构自己的“制图学”理念。这不仅是因为童年时代对海湾战争和波黑内战报道的印象构成了我报考国际政治系的最初动力,不仅是因为我在大学时期曾极大地受到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以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更因为战争这种特殊活动自身的属性——如同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继续”,是人类最复杂群体活动(政治)的一种激烈程度最高,也最不为日常生活秩序所约束的呈现方式。一场战争开始之后,所有常态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无常的命运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裁断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力、最卑劣的出卖,都会在战争进程中一一浮现出来。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感受,当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亲身经历过漫长而残酷的围城战之后,他用一个二元对立式概念来命名他的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24个推荐 粉丝2499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