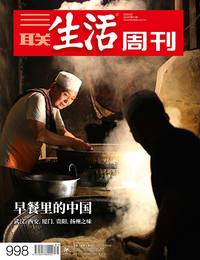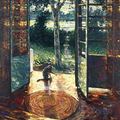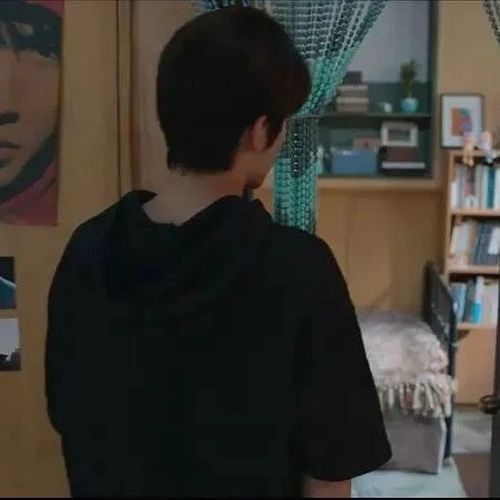厦门:不鲜不食古早味
作者:驳静
2018-08-02·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815个字,产生3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吃海,古早味
比照起西安或者扬州来,厦门还是座“新”城,厦门人时常提到自己是移民,父辈从泉州或漳州迁至厦门,或者干脆说“我们是座移民城市”。写吃食的古人,万难料到几百年后,这里会崛起一座港口城市,它的口味立足东海,又远迎南洋。
按照这个逻辑再提厦门“古早味”,仿佛有点过意不去。古早只好同现在来比。闽南话里的古早,大意就是古旧、早远。这个词原来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台湾文化流行浪潮波及全中国后,也惠及了“古早”,中文语境张开怀抱迎接了它,乃至,用到今天又成了个被滥用了的词。
老厦门人心目中的古早味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朱家麟教授说其实就是“先辈吃过的味道”。柴火灶时代,调料和烹饪方法都非常有限,同样有限的还有捕捞技术。厦门人靠海吃鱼,偏爱小鱼小虾小蟹,虽然这也与早前航海技术无法深入远洋捕捞大型鱼类关系密切,但一来中国人不怕挑拣鱼刺,二来,相比而言,肉质鲜美程度自是小型鱼类胜出。所以,一份样貌皆原始的古早味厦门早餐佐粥吃食,得算是酱油水煮小鱼。
酱油水,厦门人也叫“豆油水”。红末葱头率先进入热烈的油锅,爆了锅,再倒酱油。闽南人下酱油有讲究,酱油用泼的,泼到锅沿,沿热锅下流的两秒钟里,焦香味散溢而出。怕酱油太多,复又兑水,又怕水多,再加点盐。盐下去了,咸才是正味,对比之下,酱油反而主要为了赋香。焦香、酱香、豆香,光是酱油就有三种香。闽南人此时还会加一点糖,这个咸就活泼起来。
酱油水就成了。
能用酱油水煮小鱼来过粥,在朱家麟这样的老厦门人心里,算是有钱人的生活。一般人家,过粥也就是个酱菜。因为能来得及吃上一碗现做的酱油水煮小鱼,那说明家里头有佣人,一大早从市场买回来新鲜的鱼。而主人家自己,能悠悠闲闲,舒服睡到八九点。
在酱油水煮的小鱼虾蟹当中,以巴浪鱼最普遍。
按厦门渔业史专家陈复授的回忆,“70年代,巴浪鱼极多”。朱家麟几年前从《厦门晚报》总编辑一职上退休后,也回忆起自己儿时“赶海”经历,“我家离海不过300米,困难时期,家里头一半的蛋白质都是我赶海捡获小鱼提供的”。因而其所著《厦门吃海记》中,朱家麟也写巴浪鱼,说在寡油绝腥的时候,“天赐贱价巴浪鱼”。可见此鱼之普遍。
厦门巴浪鱼“鲜吃”,除了做在酱油水里,还有种做法是“煎”。常见早餐粥的配菜,因而还有煎巴浪鱼和煎带鱼。
厦门黑明餐厅创办人张淙明曾因“早餐爸爸”走红——2013年前后,他每日在微博发布当日为女儿做的早餐图片,最后发了800多条,“几乎没有重样”,引发媒体和美食圈关注。在他为女儿做的早餐里,就有上述两样。
鲜吃不尽,剩下的巴浪鱼就只能拿去晒干。朱家麟告诉我,巴浪鱼先蒸熟,连日暴晒,鱼干就成了。从前人们自己买来鱼自己晒,“窗台、阳台和屋顶,都可做摊晒之地”。如今在厦门著名的“八市”(第八菜市场),自是能买到鱼干、海蛎干等各类海产干货,它们皆可被厦门人引入早餐。靠海吃海,这句古老格言体现在厦门各式早点中,巴浪鱼之外,还有更为丰富的海产品,这也是生活在这座港口城市的普通厦门人,从海里最容易得到的馈赠。

汤汤水水暖人心
厦门天气热,需时时补水,因此三餐都吃粥的也大有人在。粥是居家常食之物,讲究人家区分早餐和早点,吃完“早上的正餐”,出去溜达一会儿,到了半晌午,还要再补一份早点。这时候面线糊和扁食汤就出场了。
盛扁食汤所用之碗通常宽宽浅浅,半大的敞口浅底碗,一碗也就能装十个八个,精致小巧,“就是吃着玩儿”,做不得数。同样地,闽南人不会将面线糊当作正式早餐来吃。朱家麟介绍说,半晌午,富裕人家要为老人家上点心,带鱼煎到酥脆,配上一碗面线糊。主妇早上从市场里回到家,犒劳自己一碗面线糊也是有的。
但面线糊身上最要紧的一个关键词其实是“平民”。
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设为《南京条约》所辟5个通商口岸之一,厦门码头立时繁忙起来。凌晨3点钟,码头灯火亮起,苦力们睡眼惺忪摸到每天都来上工的码头,跟摊贩那里买一碗面线糊——比苦力起得更早的就是这些摊贩老板们。
面线糊这碗热气腾腾的东西,打底的就是面线。过去那些米粉作坊,都有些零碎粉面,扔了可惜,拿去喂猪也可惜,就卖给摊贩。将这些一煮即烂的东西搁汤里,加一点猪血、大肠,撒一把海蛎,总之今天有什么,就往锅里下什么。末了切一把芹菜调和浑浊之气,特别是冬天光景里,最后撒入的胡椒更是暖融融叫人受用。
“海鲜大叔”陈葆谦是菜市场的常客,他告诉我,菜市场也多半会有一两家面线糊店,店主为了增加汤的鲜香,可能就会跟隔壁讨要或购买制鱼丸余下的水——鱼丸做完后需要用五六十摄氏度的水来定型,这“定型水”不拿去做汤的确可惜了。

这一碗汤水下去,得多舒坦。
苦力一天的劳作就由面线糊开启。朱家麟跟我分析,旧时厦门苦工分两类,一类从第二市场出城,去农村运蔬菜回城卖。还有一类在码头等着货船入港,上船扛包。而这碗汤水,有碳水化合物,作为启动身体的能量;蹬车出城也好,扛包下船也罢,立时三刻就要流汗,水分也是急需品。补水、补盐、补能量,最便宜的东西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码头工绝迹,面线糊却流传了下来。
厦门开埠之前,先后有泉、漳二港在前,二港式微,厦门后来者居上,逐渐成为闽南地区的中心。不只如此,我在厦门时跟不同的人交流,言谈间他们还会开玩笑,“外面的人都以为厦门才是福建的省会城市”,甚至,“福建是厦门的省会”。固然是玩笑,也足以见得厦门在福建省的地位。
这让我想起我还未到厦门时,电话那头颜靖跟我说的话,“你一说厦门面线糊如何正宗,泉州人会头一个跳出来表示不服气”。颜靖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本来就壮实、好吃,后又在食品行业钻研多年,吃东西最讲究食材质量。在他眼里,最好的早餐店得在市井街巷,它们的店主多半经营几十年,不开分店,大浪淘沙坚持到今天。
“原豆香小吃店”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作者


驳静
发表文章215篇 获得26个推荐 粉丝1126人
j'écris, la nuit tombe, et les gens vont dîner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