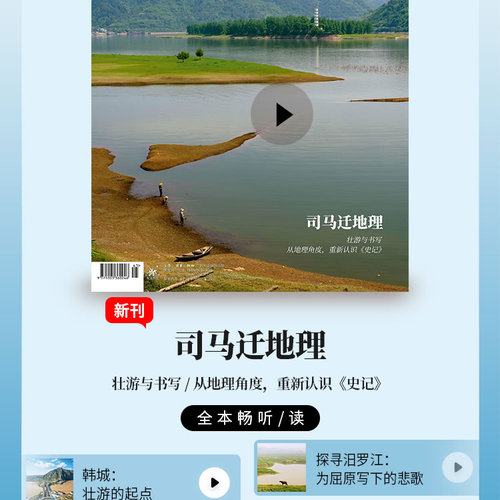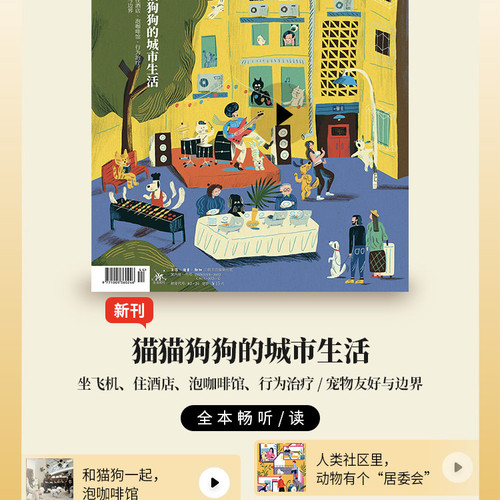《收租院》:拒绝终极解读
作者:曾焱
2018-02-24·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555个字,产生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收租院》大型雕塑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 )
展望、隋建国、向京……几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里比较活跃的雕塑家,都出现在开幕当天的观展人群里。对于艺术界,《收租院》其实早就从历史语境里“复活”过来了:上世纪90年代,《收租院》的艺术价值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收租院》而引起的学术事件和话题,甚至超出学术界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当时这一波对《收租院》的集体再观看,无疑是源于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因了他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引起一轮艺术论战和著作权官司。时隔12年,这一艺术事件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里的“是为记”而沉寂,原创《收租院》却慢慢从沉寂而至热闹,近年在国际、国内多次获邀参展。炎黄艺术馆馆长何炬星的看法,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展览的初衷。他告诉本刊:“我们选择再次展览这件作品,是因为中国艺术总要用一种力量呈现出来,并且这种力量是可以被世界讨论的。我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先生两年前在上海讨论到这个问题,当时就定下要做《收租院》展。不仅是对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回顾,也在讨论它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影响力。”
现在展示的这组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最重要的一件藏品。“在原作者的概念里,这件作品也等同于原作,同样享有著作权保护。”馆长冯斌对本刊说,“泥塑《收租院》1965年6月开始创作,同年9月完成,10月对公众开放,12月到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在北京是怎么展览的呢?泥塑已用石板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只能由四川美院派几个原作者,会同中央美院雕塑系的老师一起,对着照片在中国美术馆的现场复制了几组。后来每一次展览都是这样重新做出来的。六七十年代《收租院》在广州、上海等各个地方展览时,有些是四川美院派一两个原作者参与指导,有些根本就来不及去人,都是当地的创作者对比着画册和照片就做了,就像当年移植现代样板戏一样,京剧变成沪剧、川剧、豫剧。这也为后来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引起争论埋了伏笔——在当代艺术的概念中,这种挪用、借用和复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可能很难有一个答案。”
为了让自己能作为原创者区分于无数的复制者,1973年四川省文化厅给上面写了报告,要求国家拨款在泥塑原作基础上进行“复制和再创作”,另做一套《收租院》出去巡展。上面拨了36万元,并为此专门在四川美术学院建起一个雕塑工厂,成立创作组,集中所有能调动的资源精雕细作了4年。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创作是极为常见的方式。冯斌说,19个原作者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复制再创作,最终在1977年完成一套用玻璃钢制作、镀铜表面处理,艺术处理与表现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收租院》群雕。但此时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组《收租院》群雕自完成后一直堆放在仓库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选出一部分公开展出。“你现在看这组雕塑的外观,颜色有些偏绿,有些偏红一些,就是这个原因。”直到2000年,复制的《收租院》在四川美院美术馆才实现了整组群雕完整展出。这个时间点,也是《收租院》成为学术事件和话题的开始。
文章作者


曾焱
发表文章58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132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