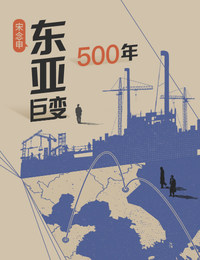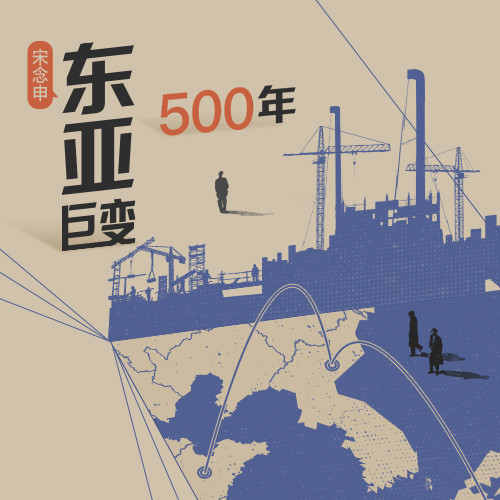引言:发现东亚现代,想象亚洲轮廓
作者:
2022-06-27·阅读时长5分钟

大家好,我是宋念申,在进入正式的讲解之前,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内容构成。我把东亚现代的故事,分成以下五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想象亚洲的轮廓:何为亚洲?何为东亚?
首先,我们要把东亚或者亚洲的概念,来梳理一下,看看这个外来的词汇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思考中的。这其中也包括中外交流中所使用的中国、朝鲜、日本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在相互对话中的呈现。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亚洲人的创造,它也不是一个自然、客观的概念,而是带有极强的人为色彩。所以,亚洲永远是处于某种参照系统中的,是让别人确信他们自己身份的一面镜子。只是这面镜子,时而被妖魔化,时而被浪漫化。
第二部分:东亚新身份与天下新秩序
进入正题之后,我们先从区域政治变化入手,看看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东亚区域格局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又带来哪些新的问题。这一部分我会从明末壬辰战争,讲到满洲崛起,看看这些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如何重塑了中国,重塑了这片区域的权力格局。再把它们放到全球视角下,看看新的天下秩序和新的政治身份的形成。
第三部分:当东亚遇上西欧
接下来,是东亚与西欧之间的系统性交流和碰撞。这一部分我会讲述耶稣会士在16世纪到17世纪在东亚的遭遇,来探讨大航海之后,欧亚之间极为重要的思想“相遇”过程,以及这种相遇带来的遗产。
第四部分:当东亚进入全球化
这一部分,我们来看看早期全球化时代,以贸易串联起来的东亚与外界的物质交往,以及随着政治变动、东西交流、贸易勃兴而来的东亚思想界的内在变化。到了这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为什么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几个方面来说,16世纪都应该被视为是东亚现代的一个起点。
第五部分: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
这一部分,我会快速梳理一下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的东亚历史。这段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东亚世界经历了各种屈辱、战乱,和抗争。这100多年,也是我们经常用来为东亚文明定性的坐标。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线,把这100多年放置到16世纪以来的较长时段中,会得出什么样的理解呢?
欧洲现代性的入侵,导致了传统秩序的崩解,但是新秩序的萌芽,也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双重滋养下诞生,直到亚洲或东亚的概念,获得全新的意义。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其实是18、19世纪以来的殖民史、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史、二战以来的民族斗争史,和冷战以来的对抗和抗争史的多重叠加。东亚世界展现了和其他区域不太相同的探索路径。而要理解这种差异,我们必须回到16世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亚需要重新被发现。
以上就是这门课程的内容构成,通过这几部分的讲解,我们试图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里使用的“现代”,是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概念。我们日常所说的“现代”,往往指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势力扩张而到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特别是冷战以来,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更成为一种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义论述。我把这种狭义的现代观称为“殖民现代”,它只是多元现代化道路中的一种。在殖民现代语境中,“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而带有强烈的时间性和种族性。
我试图梳理出一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为参照的“东亚现代”,并把这个现代的起点,定为16世纪。不以欧洲为参照的意思,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以全盘否弃;反思欧洲中心主义,但也不塑造一个东亚(或中国)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欧洲、亚洲、美洲乃至非洲的多元的现代历史,都可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也不遵循同一种发展逻辑。同时,这些观念和逻辑又不是各自孤立的,人类的现代状况是它们相互影响、吸纳、对抗、对话的结果。
本课所关注的对象“东亚”,主要是指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这块地域。
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各自有着很强的历史延续性,而且都形成了今天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国家。但通常的历史课程,往往把中、日、朝·韩分开讲述,强化了晚近才形成的民族国家边界,容易过度强调三者之间的差别,而忽视它们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东亚社会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密切关联。而本课则采用跨国史、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挑战僵化的国族边界,拒绝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个孤立单元的拼贴,而是通过关注人口、殖产、制度、思想的跨社会流动,探索东亚社会的有机互动。
美国史学家杜赞奇曾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进程,只有放在东亚区域中,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一进程一起观察,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本课程即大致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需要事先提请注意的是,今天的中、日、朝·韩,和历史上中、日、韩的并不一致,听众朋友们应避免用20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去套用16到19世纪的状况。明清时代中原、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当然有各自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相互交叠错落,不是像今天的边境、护照那样界限清晰。最近不少著作都在谈“去中国中心”,突出半岛和列岛在明清之际产生的独立于中原的身份诉求。我想指出的是,它们当时“求异”的努力恐怕和“求同”的努力一样大。我们不应把这种身份与以国籍标志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描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正是这门的课程的任务之一。
与此相关,我也恳请大家不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这些概念作本质主义解读。本质主义假定在“外部文明”到来之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土”(indigenous)传统。常有论者致力于向内寻求中国/东亚的“核心”、“精髓”,以找出一套独特于西方的文教制度,比如汉字、儒家,以及(本地化的)佛教等等。可是文化一刻不停地在变化,总在内外互动中吐故纳新——就好像源于印度的佛教被逐渐内化成本地信仰一样。我们今天认为的“传统”,大多是到了晚近才重新发现或发明的,很多特征是参照“西方”而刻意塑造的。这种逻辑和殖民现代性逻辑一致,并不是历史实相。本质主义的“西方”和“本土”,就像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看似对立,实则是一体之两面。
“东亚”、“中国”、“日本”、“朝·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这些概念是在区域内部交往以及区域与外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塑造它们的过程远没有结束,未来也一定会有旧的内容被舍弃、新的内容增添进来。唯一不变的,是对它们的不断地定义、否定、再定义。也正因如此,关于东亚的历史书写,乃至任何历史书写,都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所以,这个课程所呈现的,远远不是定论,而是思考的可能。
从下一节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现代东亚的发现之旅,我们将从“东亚”以及“中国”“日本”“朝韩”这些概念开始讲起,期待你的收听。
转发与分享|探寻东亚往事与世界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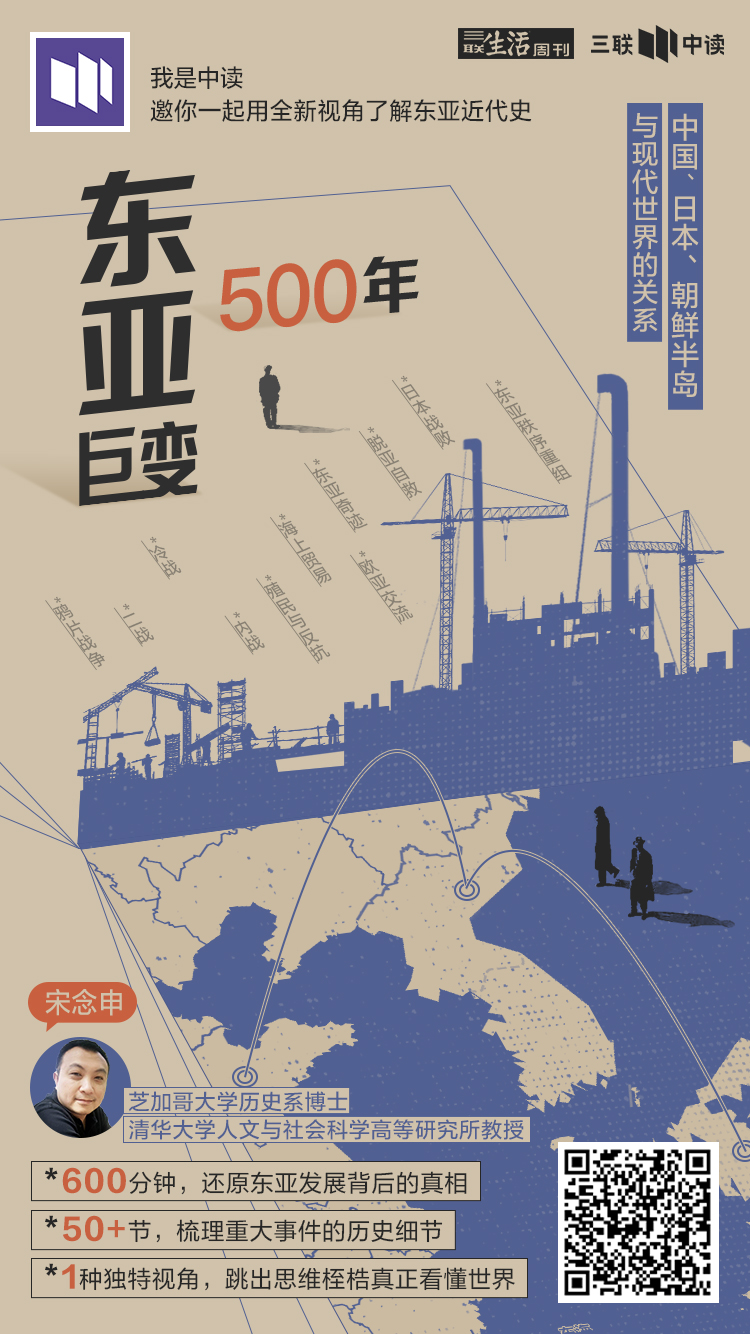
文章作者


发表文章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